

本期嘉宾:谢晶
曾留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师从Vincent Descombes,Claude Imbert,Bruno Karsenti等法国哲学家研究现当代社会哲学,曾担任法国高中毕业班哲学教师,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合作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研究专长):现当代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结构人类学。
求学之路
Q1、您曾在复旦校园度过本科四年,也曾留学巴黎,对您来说是否有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课程?
关键词:EHESS seminars学术共同体
我读博的学校——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它没有本科生,只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所以它更像一个研究机构。二战后,一些“年鉴学派”学者创立了这所学校,它从建立之初就有跨学科的特点,在这个学校里没有狭义的课,而只有seminars意义上的课。
这些课几乎没有以系统知识或者说思想史为内容的,绝大多数课的题目都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涉及不同学科——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甚至于神经科学,许多课都是好几个学者一起开的,就像一个研究团体一样,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有时同一门课一开就是好几年。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要如何选课和上课。
我的博导Vincent Descombes的课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从事学术的方式可以说是在他的课上慢慢习得的。比如他在至少两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围绕“identity”在开课。每年开学他都会花不少时间先将问题呈现出来,这个问题往往是一个很当代的问题。比如,在当代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里面常常用到集体同一性或者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概念,他说“我不理解什么叫集体身份”,这个问题看上去没什么高深的。但接下来,为了解释为什么不理解集体身份,他会花大半年时间从特修斯之船讲到维特根斯坦的同一性标准,从洛克的personal identity讲到利科的ipseité,从精神分析讲到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大家基本都在半途就晕了,晕过之后才会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很深,因为identity在Descombes的“调查”之下确实呈现出很多层意思,彼此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这使得社会科学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往往是成问题的。
上了几年课后,Descombes就出了Puzzling Identities这本书。所以我们在课上不是学知识,而是现场看他生产思想。这对我影响很大:原来思想史还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哲学研究应该是一种“调查”。就好比参观一个城市,比如罗马,你可以带着本导游书,把罗马的名胜古迹都看一遍,拍一遍,然后说,我去过罗马了(并且以此刷存在感),这是一种思想史研究,但也可以带着一个问题,比如Bernini的风格变化,因为他的作品遍布这个城市,所以就好像整个城市被一种特定的线索编织成一个网,当然这个线索不是城市本身的历史。就好像一个地方有凶杀案,如果你是侦探,你需要为了破案而调查当地的人和事,你的逻辑和这些人和事本身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此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我们一群“脑残粉”很多时候上完了课不舍得走,就好像电影散场之后意犹未尽一样。我们会站在校门口继续讨论,有时还会到对面的小酒馆里面边喝边聊。当然最开心的是Descombes也加入进来。我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意识到何为“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学术共同体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大家关心的是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大家的references也一致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展开讨论,而不需要任何澄清概念,澄清问题,或者分析文本的准备工作。这非常难得,也是我现在仍然非常怀念的氛围。
治学心得
Q2、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社会哲学这个领域?它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关键词:社会土壤社会学洞察社会科学本体论
首先,社会哲学本身不是一个领域。所谓“领域”,是这样一种对于社会哲学的定位:社会哲学就是以社会为对象的哲学。这就好像哲学里面分成很多的分支,比如法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等,每一个有自己负责的对象。如果你从事社会哲学,那么你的对象是社会,更确切地说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的实质。确实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哲学理论,比如模仿论(社会现象归根结底在于模仿),契约论,交换论,集体意识论,机制论,等等,它们之间会互怼,因而也就形成一个体系。
这种对于哲学分支的理解使得学者像到菜场买东西一样选专业,这里有人卖法哲学,那里有人卖社会哲学,还有一个摊子卖形而上学的,我觉得哪里的菜看着诱人就买什么。但这不是一个在学术上做选择的充分理由。社会哲学对于我来说,首先是一个考虑问题和展开思想的视野。因此说它吸引我所以我选择了它不太确切。就好比你要跟一个人过日子,当然如果你很讨厌他是没法跟他过日子的;但仅有吸引也不足以构成你跟他过日子的充分理由,跟一个人过日子意味着愿意以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生活方式去共同展开生活中的一些很重的经验。从事某种哲学,是说我们身在其中来认识和思考世界。
在什么意义上社会哲学是一个视野?最能体现这种视野的可能是涂尔干学派的“范畴的社会史”的工作,以及杜蒙的“社会学洞察(aperception sociologique)”和“彻底比较(comparaison radicale)”。总的来说,这些工作都提醒我们注意到,任何的观念都扎根在一定“社会土壤”里。比如今天对于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来说非常核心的“person”的概念,莫斯有一篇文章分析它如何从“面具”一步一步变成意识和法律的主体,并且与其它社会传统中对应的概念做比较,这使得这个看似与主体哲学捆绑在一起的概念马上变得既丰富又脆弱,因为它的内部存在的张力和矛盾,因为它并不是哲学家能够一劳永逸作出界定的,而是特定社会群体中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背后的一个很重要,但并不总是被意识到的前设。
当我说“社会学洞察”,有几个误解需要排除。首先,我的意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其实哪怕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都已经充斥着观念了,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社会学洞察不是一个很粗糙的社会决定论。
另一个是将之视作相对主义,比如说西方人的person概念是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对自己负责的,参与到公共讨论中去的主体,它具有法律、心理上的地位等等;而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没有的概念。这是比较哲学的一个通常做法。“社会学洞察”并不是要为了证明不同而证明不同。
还有一个误解是说,这无非就是在考察观念史。事实上,社会学洞察尤其要求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观念视作是一些“实践观念”,或者杜蒙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们所支撑的不是一个思想体系,而是一定群体的生活方式。这里的“生活方式”要从维特根斯坦的form of life的意义上来理解,它是一个机制性的总体,它是具有规范性的。
在这第二层意义之上,还有第三层意义的“社会哲学”,我会将它称为“社会科学本体论”,总地来时,它是要将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传统,视作一种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
但这个问题要深入,涉及到很多问题:启蒙以来建立在抽象的人之上的政治哲学,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界定,中国社会理论研究在我看来的误区,等等。这个访谈的初衷可能不是讨论这些学术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最近出的那本关于法国社会哲学的书,从导论到结论,正好是我从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哲学”渐渐过渡到第三种意义上的“社会哲学”的过程。
Q3、在研究领域外,您有哪些爱好?是否也会对您的研究有启发?
关键词:杂食动物put into perspective
我的兴趣和很多学者(文青)一样,无非是小说,电影,音乐,旅行,徒步,等等。我是一个杂食动物,“文化消费”也没有什么章法。至于对我的研究有什么启发:玩就是玩,不想着研究。但反过来说,如果研究不只是一个领域,也就没有什么内外之分。比如,审美经验不仅能带来身心愉悦,而且可以提升我们的批判能力和方法论上的自觉。在我工作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想到比如说Kubrick和Terrence Malick这样极端完美主义的导演,Maria Callas和Natalie Dessay这样的表现力甩同行几条街的女高音。能够体会到Woody Allen和Kubrick之间的距离,可能就会在完美主义(强迫症)的路上走得更远。刚才讲到治学的节奏,有两个经验令我对节奏体会很深,一个是自己生孩子的产程,还有一个是看黑泽明《七武士》的时候,很神奇的是,这些都很有助于我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到达了哪个节点。很多经历都有相通的地方。徒步的节奏和读文本的节奏也有相通的地方,一个文本不是一马平川,不能均衡用力,有些山头,要花很多时间,很耐心很小心的过,但是爬到顶,整个的文本可能就在眼下了。
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我确实需要出去走走,看一看不一样的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风景,耐心地沉浸到自己不熟悉的城市,这是我“开心”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打开自己的过程,学问会越做越小。我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需要被put into perspective,学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practice,它本身需要被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面去,否则,那些精细的工作(比如花一个月的时间去打磨一篇文章)会越做越不知道在干嘛(更不要说开会报账了)。
从教初心
Q4、您曾担任法国高中毕业班哲学教师,这段经历让您有怎样的感触?您又是如何看待法国哲学教育呢?
关键词:公民教育“奇特”的哲学课
原则上,法国哲学教育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政治实践。它的真正确立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也即19世纪末期。当时开设哲学课的目的在于共和教育,也就是要培养公民——这些公民是自主的,能够对自己负有道德、法律等各种意义上的责任,尤其是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因此,他们需要具备清楚表述并且参与讨论的能力。比如在新冠肺炎占据所有讨论空间前,法国人正在讨论的是退休改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12年奥朗德上台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过程,当时所有人,无论什么场合,都在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整个社会。设立哲学课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培养公民理性讨论的能力。这是原则,但实际上,确实像王春明老师所说的那样,是课程就得考试,为了考试拿高分,它就变成一个三股文:正题、反题、合题,还要加一个“帽子”——导论。这就是他们高中哲学论文的写法。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效地呈现自己思想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法国哲学教育原本是应该围绕问题和概念展开的,但在今天的法国高中里,绝大部分的老师还是在讲思想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笛卡尔等等,一直讲到梅洛-庞蒂。这种思想史授课的路径,很明显与培养有对话能力的公民没有太大关系,除非学生将来想成为一个哲学教师(或者提升自己的逼格),它没什么用。
我当时在高中毕业班里做哲学教师,是一段很奇特的经历。因为我自己刚刚“八年抗战”写完博士论文,而任教的中学本身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中学,它是给考了好多次都考不过的那些人最后一次机会的一个高中,所以都是一些“学渣”,而且这些“学渣”五花八门,他们的社会背景、学习能力各不相同,有离家出走的富家女,还有戒毒所刚出来的,还有很多二代,三代移民,生活在巴黎郊区的一些廉价公寓里面,所以这些人来上课的第一反应是,“你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跑来跟我讲哲学,哲学能干嘛,能吃饭吗?”有一堂课我跟学生讨论宗教的问题,我一上来说“像圣经这样的神话故事……”,学生就“炸”了——你怎么能说这是个神话故事呢?对比这段经历,我觉得现在在复旦上课非常comfortable,因为下面的学生把你的话当成“圣旨”一样听,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度,我倒是更倾向于那些学渣的态度,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得向他们证明哲学到底有什么用,至少它到底有意思在哪里。
那一年,每一次进入课堂我都很紧张,我都在想这堂课会不会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涂涂指甲油,刷刷手机?会不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摔门走了?从那一年开始,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上课方式,我要想办法把一个哲学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意义的这个事实呈现给他们。所以,我会讨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对于他们的年龄段来说,“自由”的问题他们都很感兴趣;或者是平等的问题,因为他们来自不一样的社会阶层,所以对平等的问题也很敏感;或者是宗教的问题,因为在法国这样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问题同样很敏感。这些问题每一个其实都足以成为“调查”哲学史的线索,我也可以在讨论中逐步教他们如何以有效方式(也就是“三股文”)组织自己的想法。
公布高考成绩的那一天,我们几个老师在中学门口等他们的消息。有一个学生在二十分的哲学考试中拿到了十五分,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很高的分数。我祝贺她的时候她说,“Madame我想好了,我要到索邦念哲学。”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我想,我没有从柏拉图讲到梅洛-庞蒂,但我的课没乱上。现在在复旦,我也坚持用这样的方式上哲学课。并不是因为这是最好的哲学教育方式,而是因为这是我的经历,我的导师就是这样教我做学问的,我觉得这样的学问是鲜活的,我自己乐在其中,学生就不仅仅是在学知识。
Q5、您所讲授的二模课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广受好评,不少同学认为“干货满满”,不过也有部分同学认为门槛高,“难度有点大”,您是如何构思这门课程的呢?
关键词:读经典方法论预期
门槛高这个“锅”我肯定不背。我每一次上课时都是诚实地告诉学生,这门课可能会很烧脑,但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知识性的基础。一开始的两堂课类似于电影预告片,如果学生觉得有意思的,那么我希望他们能抛开杂念快乐地跟着我烧脑。就像从事自己喜欢的高强度的体育运动,很累但很爽。
这个课的目的是很简单的,既然是读卢梭的文本,那么就是“读”,而且不是我读,是学生们读,当然,课的名称叫“西学经典”,那么我们在读的过程中至少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它会成为经典?所谓经典,意味着它对我们今天的思考还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既然它是西学,不是我们传统中的经典,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去思考一些问题?
我的工作,是帮助学生们读,有很多的elements,学生自己是get不到的,第一种是概念上的elements。比如政治、自然、不平等,甚至是人,这些基本概念,都有自己的社会土壤、历史土壤、思想史土壤,必须要做好澄清工作,如果一个学生停留在汉语的“政治”概念,而不了解politics的词源,那么他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理解这个政治哲学文本。
第二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elements。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自然法学派或者什么是社会契约论,也不太读得懂这个文本。举个例子,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大意是“第一个跑出来圈出一块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群足够愚蠢的人来相信他的人,就是市民社会的第一个奠定者。”这句话如果不交代思想史,大家不知道他其实“怼”的是洛克。
此外还有一些彩蛋是学生自己看不到的。例如,卢梭在一开始致日内瓦共和国的献词中说,如果我可以选的话,我想要自由的生,自由的死,也就是说,我需要服从法律,它是如此崇高,以至于我或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去震撼它的枷锁。这句话是很矛盾的——我想要绝对的自由,但自由意味着服从法律,而且这个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自由观有多奇葩!但是学生很可能看不到这个矛盾。包括在前言里面那句很有名的话:自然状态是现在不存在过去很可能没存在过将来也很可能不会存在的状态。都不存在那是个什么状态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界定。刚才提到的那句怼洛克的话,大有文章可做的是“并且找到一群足够愚蠢的人”,但这句话别说是学生,大多数学者都不会自己注意到(我也不是自己注意到的)。类似这样的彩蛋肯定需要老师来引导。
如果说我这门课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预期,那是因为我希望学生能体会到,读书,跟写作,跟思考问题一样,是有节奏的。一开始会很慢,因为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都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我的第一堂课往往连题目也审不完,但是慢慢地,就像是Ravel的Boléro一样,不同的乐器一个一个加进来了,此起彼伏,就会有渐入佳境,水到渠成的感觉,以至于读着一句话,好像整个文本都清晰地呈现于脑海。
以上是“读经典”的基本层面。在此基础上我可以在自己的Boléro里加其它的乐器,这取决于学生的进展。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自由的表面上的矛盾,只有读到《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八章才能理解卢梭的意思,又比如卢梭是一个怼天怼地的人,当他怼霍布斯,怼洛克的时候,最好是去读一下霍布斯和洛克。但直接把这些补充材料全景式地呈现给学生,这只可能使阅读变得毫无惊喜,索然无味,因为你不是在“调查”,因为案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另外,到了每学期尾声时,如果我觉得学生(只可能是一部分学生)对于文本掌握得很充分了,我会考虑把大课提升为seminar,也就是说谈论一些我自己对这个文本乃至卢梭思想的见解。就像古典音乐里面有华彩乐段,摇滚乐演唱会里面有solo的部分。所谓的华彩乐段和solo,跟整个的交响乐或者说歌剧或者说演唱会的曲目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是个人色彩十足的。我觉得这样学生或许能看到,扎扎实实地读好文章,接下来有很多有趣的事可以做,“调查”无止尽。比如,如果我们比较《二论》里的社会契约和《社会契约论》里的社会契约,就会意识到后者只可能理解成一个fiction,它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而是从逻辑的角度提出的。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像有些学者那样反驳,实际上社会契约不可能这样产生(这是侮辱卢梭的智商)。但是恰恰是从逻辑的角度,它是有问题的,卢梭可能自己意识到了,所以才有了第二卷里没有立法权的立法者和写在人心中的第四种法律,等等等等。
疫情感悟
Q6、疫情期间,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有怎样的感触?
关键词:反思生活共同体应对
作为学者,这次疫情对于我们的影响其实还好,我们不是那些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不是那些因为疫情而失业,甚至于经历经济危机的人。我的日常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都是不值一提的。不过,我倒是想借此说说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我们每个的人的生活确实都在受到影响,比如原来要开的会可能开不了了、原来要写的文章交不了了、原来应该是跟学生面对面上的课现在变成了网课了、原来伸手可及的书现在因为“隔离”在外读不到了、原来约定重逢的日子现在变成猴年马月了,每个人受的影响不一样,但它们都能使我们反思,原本觉得天大一样的事原来不做天也不会塌,原本觉得可以推迟一下的,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真的看重或渴望的东西。这些触动,等到生活恢复了常态还是得记着。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价值重新排序,对生活方式进行反思。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像这种公共的,乃至于全球性的突发事件,应该引起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从共同体的层面应该怎样去应对?进一步的,我们到底想生活在什么样的共同体中,我们共同体的价值观是否需要重新排序?
疫情是个悲剧,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代价应该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很多哲学的经典问题,比如它再次证明西方的人权政治有很大的局限性,又比如我们对于科学的信仰,“确定性”这个概念本身,乃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运气很好,“隔离”在一个可以观察到自然界的地方,每天森林都变的更绿,院子里的花都开多了一些。它们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病毒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它跟我们是共生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具有灾难性的那些代价,究竟是如何酿成的,它们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用何种价值标准衡量出来的代价?(比如,哪个国家GDP负增长了,地球是不care的,只有那个国家里的一撮人很捉急)令人细思极恐的一种可能性是,产生这些灾难的原因是否恰恰是令我们将它们视做灾难的原因,换句话说,恰恰是我们受到一定价值观推动而从事的行动,酿成了我们用这些价值观衡量出来的灾难。
彩蛋问题大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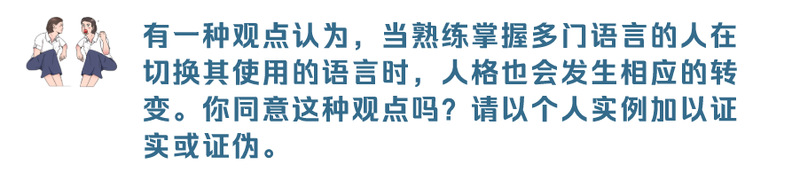
这个观点有两种诠释方式,一种看上去很酷炫,但其实很荒诞。我猜王春明老师是在这个意义上表述这种观点。它有两个前设,都是结构主义的前设:第一个前设是说,每个语言都是一个体系,语言和语言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第二个前设是结构主义用来“怼”主体哲学的,即“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或许大家都有所耳闻。列维-施特劳斯《神话逻辑学》中说,不是人发明了神话,是神话通过人来说自己。照此来说,当我使用这个语言时,是这个语言也在使用我,换了一种语言使用我,也就是换了一种思想,换了一种风格,也就换了一个我。这个观点看上去非常酷炫,但其实是胡扯,因为如果要这样说的话,一个人前一秒钟说中文,下一秒钟说英语,他就是换了个人格,这样他不是人格分裂吗?如果他会说很多语言,那他就有很多人格,就成了孙悟空可以七十二变了。这是非常荒谬的。
王春明老师让我举实例可能考虑到我的家庭是一个多语的环境。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我跟儿子说普通话;跟丈夫说法语;跟父母说上海话(假定方言也是一门语言);我跟丈夫当着孩子的面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说的是英语(为了不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意见不一致从而钻空子),所以这里有四门语言,当我们一家三口和我父母一起吃饭时,我儿子可能看见他妈妈在四个语言当中切换,他不会说他有四个妈妈,他也不会说“哇我妈妈是孙悟空啊,一直在变?”他很确定“我只有一个妈妈,她一直是那个妈妈。”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我将“人格”理解为person。中文里没有“人格”这个词语,我们平常不会说“你看这人格多坏”,只会说“你看这人多坏”,所以人格是用来翻译person的。按照上面的切换人格的说法,我们五个人每个人都至少用到两种语言,那么那到底是五个人在一起吃饭还是十几个人在一起吃饭???毫无疑问,这里只有five persons。
所以上述观点的酷炫版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在不同语言之间切换的时候,我的表达能力、我的清晰度、乃至于我的表现力,我的态度,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这是同一个person在变,而不是一个person变成了另外一个person。这是上述观点的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看上去没有任何哲学性可言了,我们身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一些变化,别说一个person,就是一个杯子,一支笔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但其实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第一个问题是我刚刚所说的语言的表达力问题,确实我们会觉得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哪怕直译出来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在不同语言中的舒适度也不一样。这是值得深究的。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问题——我始终是同一个person,但我在发生变化,由此会引出一个帕斯卡尔式的问题:这个person变到一定程度,还是他自己吗,会不会变成另一个person?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面提出这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爱的人毁容了,你还爱他吗?说不爱他了似乎不太好,因为,他应该还是他,他只是毁容了,但事实是很有可能你就不爱他了,这说明你爱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容颜,人格和容颜之间不能划等号。但问题可以变的很吊诡:如果他的性格变了呢,人生观变了呢,记忆也变了呢,变到什么时候我们有正当的理由说,我不爱他了,因为他不是我爱的那个person了。所以说王春明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很可能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人格”这个概念本身的问题,人格概念本身是有土壤的,它是推动人们行动(比如爱和恨,赋予和追究责任)的一个概念,所以它不是原子式的,被哲学家以一劳永逸的方式定义过的,大家都知道怎么用的概念,而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从直觉上来说,我知道什么是person。比如我儿子就知道,这是我妈,他不太会搞错,对吧?但要清楚地说出我用来界定一个人格的那些标准,这不是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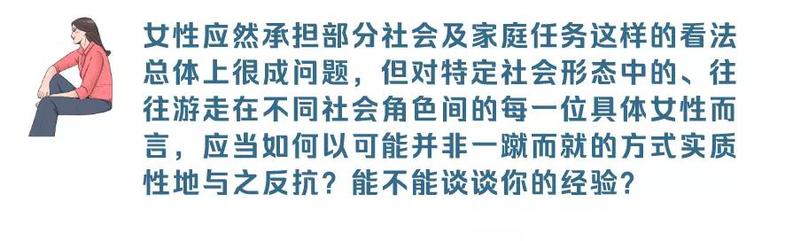
这个问题很“王春明”老师,他的句子很长,所以“信息”量很大。
首先,“女性应然承担部分社会及家庭任务”这不成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分成公共社会生活和家庭社会生活,大家都应该在这两个层面承担责任,除非你选择退出家庭或退出公共领域。王春明老师的意思应该是“男性和女性在公共社会和家庭社会中分工不平等”,就是说很多女性同时在承担这两个社会里面的任务,而很多男性仅仅承担公共社会里的责任,而不承担或者说较少承担家庭责任。这个问题很大,是一个讨论一学期也讨论不完的问题。
我很关心的是他后面的那个“但”:“但对于……的女性”。为什么他这里不用“所以”?一般的逻辑是:“……有问题,所以应该怎样反抗?”我猜王春明老师的意思是,从原则上或者理论上来说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用了“总体上”这个限定词),但实际上你想怎样呢(所以他用了“特定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位”,“具体”这些限定词)?这是很多人对于政治哲学提出的一个反驳——你们在理论层面讲了半天这个不行那个要改,但实际上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应对的方式,第一种是意志主义的方式,那就是“申权”。今天的社会确实对女性有双重要求,事业家庭两不误。“申权”无非就是说:对不起,臣妾做不到;对不起,老娘不干了。比如,我在中国接触到很多女性学者都会诉这个苦:队友在家里躺尸,但学校对于女学者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她们觉得学者也没做好妈也没当好,满满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不仅是一种感觉,而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现状。这个时候当然可以说,我要平权,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不正当的。
这是王春明老师所谓的“反抗”的逻辑。法国女性反抗了很久之后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不是因为队友不配合,而是她们自己做不到。现在她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概念叫“charge mentale”,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责任或者说是负重。作为一个女性,你会不由自主地筹划所有与家庭有关的事,因为你默认这是你的“领域”,潜意识地赋予它们至高的重要性。而男性的态度一般是:“你告诉我该干嘛,我执行”,或者说,“你告诉我能怎么帮你”(背后的预设是: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第二种回应是社会学的回应,女性接下来会意识到,自己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在社会土壤中,教育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教育,或者说以语言为介质的教育。布迪厄在《Domination Masculine》这本书中说,哪怕是走路的姿势,我们看这个世界(物理意义上的世界)的方式,其实已经受到我们性别教育的影响了。布迪厄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habitus”,即这种教化成为我们无需被意识到,无需被理论化的,最根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层面和身体的层面,我们就一直在复制男性主导的模式,以至于仅仅在话语的层面、法律的层面说“我要和你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是远远不够的。我记得好像是张寅老师说的,研究发现在那些男性和女性可以有一样长的产假的社会里(加拿大?),男性学者休产假期间的发表量大大增加。如果habitus不改变,那怕平权了,不对等的关系始终会存在。社会学的应对方式,就是把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提到一个有意识的层面。事实上哲学所作的也是这个工作,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需要被不断澄清,是因为我们提问题的方式(比如王春明老师的这个问题)中就已经有很多前设了,而哲学需要揭示“前设”,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也是这样。
举个例子,每年三八妇女节工会都会送女教师礼物(不识好歹的我一直没有理解三八妇女节送礼物这个操作),有一年送了一个便携缝纫机,还有一年是一个购物袋,你可以想想这背后的前设是什么。这个前设没有人说出来,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从小女孩到老阿姨,如果不断地收到缝纫机和购物袋,你就妥妥地形成的habitus了。我觉得这才是需要被意识到、被讨论的。
王春明老师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他有点作茧自缚了,他预设“反抗”,既意志主义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应对方式,是唯一的应对方式,然后质疑这种应对的有效性。其实还有社会学的应对方式,他不是反抗,而是理解。而理解一定是双向的。一个habitus或者刻板印象总是同时对两性都起作用,比如与女性多愁善感的刻板印象构成互补的是“Boys don’t cry”或者说“男儿流血不流泪”的刻板印象,后者也是很没道理的(“流血不流泪”如果是事实判断,好像更适用于女性),但也变成了根深蒂固的habi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