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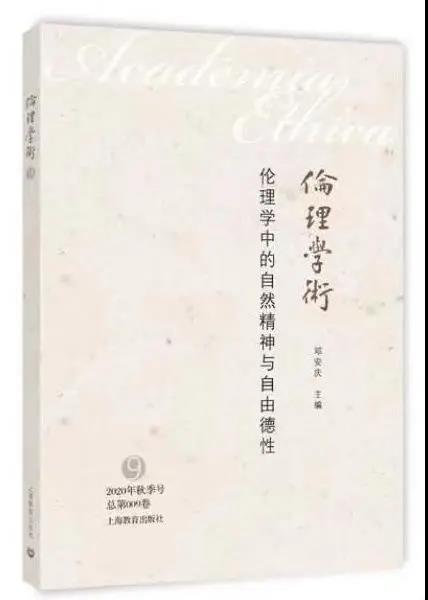
书本信息
《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
《伦理学术》2020年秋季号总第009卷
主编:邓安庆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0年12月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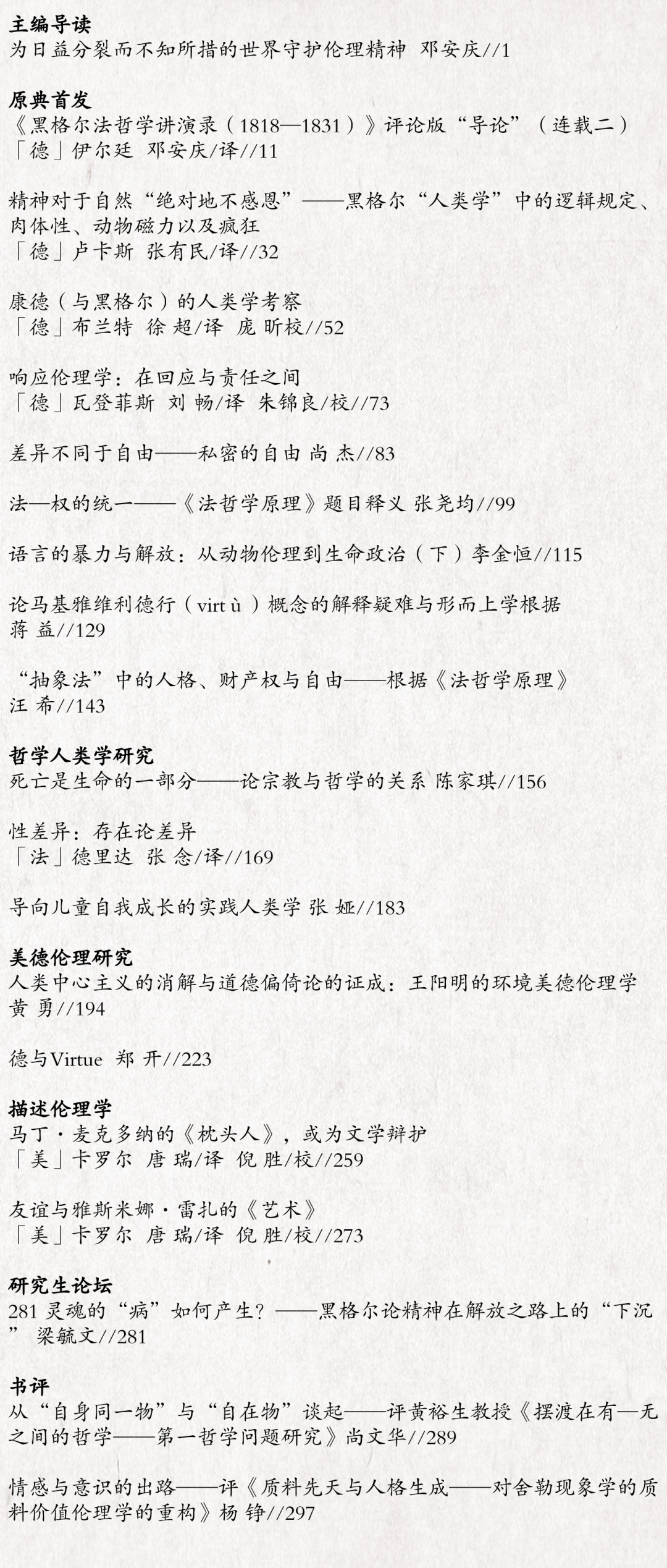
主编导读
为日益分裂而不知所措的世界守护伦理精神
邓安庆/文
人类文明一直都呈现出非常脆弱的特征,许多文明在不经意之间灰飞烟灭,从历史记忆中消失,而现存于世的文明形态也不免伴随着野蛮与血腥,有时野蛮与血腥还会被强权者包装成不可怀疑的真理,迷惑住号称追求智慧而具有最深邃思想的绝世大哲。让文明死去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一种不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而是人类看不见、摸不着却来要人命的病毒。病毒一旦传播流行开来,医学与科学对它无能为力,就演变为瘟疫,让人类顿生渺小之感,文明摧枯拉朽,人类尊严顿失。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a)虽然不会让文明消亡,但足以令世上几乎所有被人敬仰的“主义”全都暴露出自身的脆弱与尴尬,一切正常的秩序几乎全部停摆,飞机停飞,国门关闭,封城封村,这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如果说特朗普在美国的偶然上台还只是给“全球化”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话,“新冠疫情”却直接让“全球化”了的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自愿不自愿地最终都意识到了文明的脆弱性。几乎可以说,这一次文明危机绝不仅仅只是“西方”的危机,只是自由主义的危机,而必须说,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危机,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之脆弱性的危机。
如何理解世界的这场惊天之变,无疑成为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哲学号称就是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理解和把握了思想自身所处的时代,哲学才能被称之为智慧之学,才能进一步阐发如何建设未来更为美好世界的实践智慧。理解世界无论如何都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没有理解世界就着手改造世界,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而理解世界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大清的皇上们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理解世界在如何变化,了解英国当时在世上的地位,知道世上除了大清“神圣的”礼仪外还有某种叫作科学与技术的东西,也就有可能正视英国使团作为礼物送来的地球仪、天体运行仪、蒸汽机、棉纺机、迫击炮、卡宾枪等代表当时工业文明的最新成果,它们绝非什么蛮夷的“奇淫技巧”,而是正在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文明动力,就不会对英国使团不愿在皇上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吃惊和生气了。外面的世界早就彻底改变了,而唯有天朝大国视别国为蛮夷小国的傲慢未变,盛世的梦幻未变,后来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厄运也就不会那么难以理解了。
所谓以历史为鉴,实际上就是要明鉴历史上因不理解世界而遭受本不应该发生的厄运的惨痛教训。但历史就是历史。理解了世界才能知道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才能顺应历史的天命。虽然命运以某种铁的必然性主宰世界,但理解和把握这种必然性,按照必然的天道天理行事,走在正道上,才有好运之气的升腾,这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
当前,如何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突然遭遇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思想之开启的前提。黑格尔之所以成为能超越康德这样一个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现代哲学家,就在于他能洞悉启蒙哲学内在的问题,并以整个“现代性”所遭遇到的危机与问题,而不仅仅是理智启蒙问题,为哲学思考的对象。理智启蒙的确为现代性催生了自由的个体,他们作为独立的主体自由地成长了起来,这无疑代表了现代性历史的根本方向。但是,自由了的个体随之必然要求其主观的权利,这也是非常正当的要求,且具有自然法的合理基础。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英法自由主义乃至康德、费希特对于现代性规范秩序的建构,都如同休谟批评现代科学的知识论基础一样,是建立在观念之联想的极其不牢固的沙滩之上。
因而,在英国光荣地大力发展科学与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历史跨越式地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科技文明时代,现代性必须要有新的规范秩序。于是,启蒙了的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着手将现代性的观念、思想与价值变成现代性的自由的规范秩序之时,就遇到了旧欧洲一切保守势力的疯狂抵抗,法国大革命就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的转折点。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也就有了新的维度与前提。
在这里,我们无需更多地追述现代性的历史演变,只需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现代性遭遇到的文明危机已经非常多了,但之前的每一次危机,人类都能在反思中寻找到文明发展的方向,哪怕是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将国王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残暴专政,之后又出现了拿破仑横扫欧洲的侵略战争,如此等等,人类都能穿透思想与观念的迷雾而寻找到文明发展的基石与方向,从而守护着文明。但是,这一次“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文明危机却完全不同,可能是因为文明的敌人既不是来自“敌对”力量的战争,也不是蛮夷的入侵,甚至不是意识形态的冷战,而只是来自大自然的病毒!让人匪夷所思的恰恰就在于,仅仅一个不明不白的病毒就让东西方严重分裂、左中右严重分裂,让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共同体”严重分裂,甚至至亲至爱的“家人”也很分裂;它不仅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方向,而且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最终连真相也都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彻底分裂的力量难道真是病毒吗?
病毒显然只能是一个引擎,一个导火索。

一个本身强健的生命不可能被病毒击垮,就像一台能及时给漏洞“打补丁”的电脑不会被“病毒”攻破而陷入瘫痪一样,虽然这次“新冠疫情”实实在在地让社会生活陷入了瘫痪。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一个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夜之间就彻底封城,人们只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家“斗室”之内生活几个月。放在之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尽管不愿意,世界大多数城市最终都走向了不同程度的“封闭”之路。
社交生活的“停摆”,意味着许多领域的“停摆”。大家都在经历众多“停摆”的阵痛。但对于哲学而言,最感痛苦的却是思想的“停摆”。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停摆”,不是说人不再思想。相反,思想是自由的,无论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人能自由地思想。而我说“新冠疫情”令思想“停摆”,指的是之前所有的思想,似乎都成了空头支票,无论什么样的思想似乎在凶猛病毒的攻击下全都失灵了。此时,世上所有相关于“价值”或“意义”的考虑,据说全部让位于哲学最基础的问题——生与死的较量,最大的“义”就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活下去。当然,这样简单的道理不是人们不懂,分裂的更深的根源,不在于要不要活下去,而在于何种“活法”才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即对于一个人(der Person)而言,何种“活法”才是有意义的,何种“活法”简直不如不活。这种“活下去”的底线从而也适用于“死”的尊严。人都有一死,或迟或早。人世间最大的正义,就在于所有人都有一死,因而死无关乎人的意志或选择,但绝对关乎尊严。有的人活得高高在上,神乎其神,但临死时却失去了尊严,或者毫无尊严地暴死;有的人活得窝窝囊囊,但死时却死得很体面,死的尊严是生命尊严的确证。
表面上看,“新冠疫情”大敌当前,谁若让思想纠缠在这些最基础的哲学问题上,是可笑的、迂腐的,但是,如果不涉及这些问题,不以生的意义和死的尊严为依据,而单纯地讨论要不要封城封路,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出门社交,或者抽象地在要自由还是要管制之间争吵,哲学思想马上就迷失在无方向感之中而陷入“停摆”。因为在生与死的底线上,思想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本能上,理性无论如何是敌不过情绪的。情绪的反映不仅最为切身,而且最为激烈,从而也最为因时因地、因天因人、因灵因鬼,因各种固有的僵化的观念而变。所以,在此处境下我们看到了,不管任何想法和观点,都会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者,而反对者也仅仅只是因为要反对而反对,却提不出什么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来。如此这般的都因反对而反对,因否定而否定的争吵进程,就陷入了黑格尔说的“恶的无限性”。
但正是黑格尔关于如何消除“恶的无限性”之思考,开启了当前思想的可能性。因为“恶的无限性”起因于事物的有限本性,并各自封闭于自身的有限却要强装无限的自信。事物就其“存在”而言,具有逻辑上无限的可能性,而逻辑上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不能获得其现实的“定在”,即在时空世界中的“规定性”,就是“纯无”,因而,任何事物之有“定在”是就其“实存”而非就其纯粹抽象的“存在”而言,事物“实存着”即具有了存在上的规定性,并因此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个“定在”,即被规定了的实存。所以,实存是事物被规定的现实存在之进程,这种“被规定”同时也就是“被否定”的进程,因为任何一个说“事物是什么”的规定,是从否定它不是什么而来。说一个人是人,即用“人性”来规定人,就否定了人不是畜生也不是神。而反过来想把自己说成是神的人,也马上具有一种否定自己是人的危险,因为没有了人的规定性,你可以成为一尊神,同时也意味着你能成为一个畜生,这在逻辑上是同样的道理。人的定在,只在规定人的天命就是成为一个人时,这种“规定”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规定不是限制,不是专制,而是自由,是由人之本给出人成为其自身的自我规定性。正是这种自我规定性的自由,具有内在自觉的否定性,即否定他既不是畜生,也不是神,从而不会陷入“恶的无限性”。
如此“定在”规定性之有价值,在于它守护着人本。“恶的无限性”因其突破事物之根本与本体,进行“无根”“无本”的否定,最终成为分裂世界的根源。理解现代世界分裂的这一根源,是我们当下寻找文明方向的起点。
黑格尔也正是通过否定“恶的无限性”来为现代性开启新航道的。
从思维方式来说,“恶的无限性”是现代知性思维之结果。实际上,“知性”执着于概念思维,这一点黑格尔自己也是坚持的,他说哲学思维就是以“概念”来把握现实。但关键在于,知性思维执着于概念的抽象规定,见山是山,见水为水,这种思维对于科学知识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科学事关已成“事物”的本质规定,必须确定而准确。这与诗人对山水的鉴赏性描述不是一回事,后者无关本质,无关山水真实定性,而仅仅描述山水给人的主观之印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刘禹锡写下“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而说他没有反映出山水之本质,也不能责怪他把“山水翠”(或“山水色”)与“白银盘里”的“青螺”相比拟,此处如果采取知性概念的语义分析,就会导致“诗意全无”的可笑。所以,黑格尔对知性思维也是给予了高度肯定的,以概念及其语义的准确性来把握事物的真理,这对于哲学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但黑格尔高于现代哲学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看到了哲学具有超越科学的思想能力(这里的“科学”指近代以牛顿力学为榜样的现代自然科学)。“科学”从经验到的感性现象中“分析”现象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不能进行真正的“思想”的。“思想”的真正对象不是当下呈现的现象,而是现象之“存在”的原因。但知性思维显然不可能把握到“存在”本身的复杂性。“现象”是一个确定对象,即已成的对象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存在”永远不是一个“已成的”现成的东西,它是未完成的,是要在其“实存”中“存在”并逐步获得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去趋向自身的完成。因而,“实存”既有“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维度,也有“存在”的空间性、社会性,乃至民族性与国家性维度,乃至“世界”维度,如此等等,当我们要给予“存在”或“实存”一个确定的“是什么”的规定时,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何种时间性与何种空间性,乃至何种世界性维度论说其规定。于是,所有这些规定都只能是一个暂时的、不可固定下来的定在之规定,因为在我们做出这些规定的当下,时间已经在流逝着,已经不是前一刻的时间了,时间变了,空间也会跟着处在变动不居之中。

但是,知性思维固执于把每一种规定都视为事物在一切时间与空间中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定,这就出现了问题。同时,知性规定是认知的主体(人)通过其以事物的“表象”和“意识”为中介做出的对于事物的“主观的”规定,它依然不明白黑格尔所坚持的,哲学的“客观思维”乃是这样的:思维所把握的既是思维着的主体之主观的意识,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存在。但我们能从固执于自身的主观的意识,回到事物本身是什么的“存在”层面时,也即回到“真理”面前时,“恶的无限性”才可中止。这就是黑格尔呼吁哲学必须以真理为己任的原因。
目前的世界之所以处在这种相互否定、各自对立的分裂状态,原因就在于,哲学长久以来在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中回到了知性思维,即回到了主观意识对事物当下现象之分析,从而只是对事物做主观的外部反思,而进入不了事物本身的存在,并因此也就放弃了哲学的真理追求。“后真相时代”提供了当代思想在真理面前退却的冠冕堂皇的“遁词”,但“后真相”对于哲学如果有意义,不在于放弃对真相的追寻,而在于意识到如果“真相”一直在延宕中而显而不露时,我们如何有新的方式超越主观性而坚持理性思维,无论如何,“后真相”并不能为任何主观的真理提供有效的辩护。
当我们把现代性分裂与对抗的起因归咎于知性思维,即主观性的外部反思之思维定势时,我们确实在走向黑格尔的哲学之途。但只有真正深入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精神之中,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黑格尔,理解现代性,尤其是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及其为现代性所确立的新的基础。
我们赞同哈贝马斯对他的这一评价: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作为哲学来思考的哲学家。他对现代性的思考意在真正理解现代性并进而推进现代性,就他自身的思想而言,他无疑达到了真实理解现代性的目标,但他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及其为新的现代性开辟的规范秩序建构的目标,实际上在他死后立即被中断了。
当我们这样言说现代性时,我们把“现代性”(Modernität)作为现代思维范式,这就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知性思维,这种思维一方面在知识论上为科学奠定基础,寻求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求证的逻辑;另一方面在价值论上为“现代性”确立了“伦理原则”,这就是把建立在主观性自由(或主体性自由)基础上的“正义”作为现代的伦理理念;因此,现代性还必须有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实践哲学的“规范秩序”建构。黑格尔在现代性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有其超越前人的独立创新之处:在知识论上,他不满足于英国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到休谟那里实际上在知识论上就走到头了,从单个的经验知识出发,并不能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确立基础;他也不满足于康德批判主义的先验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止步于知性思维从而把“知识”划定在现象界,事物之自在自为的本体却成为不可知的领域;在价值论上,他认同并推进了个体的主观性自由为现代的基本价值,并把它视为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这个新的时代”(Die Neue Zeit)的时代精神。他比其他自由主义者做得更好的论证,就是通过对个体自由意识史的叙事,为现代个体自由价值做了详实的历史梳理:个体自由意识在苏格拉底身上明确地表现了出来,但这种自由无法上升到柏拉图的城邦伦理原则之中,“正义”作为城邦伦理原则因此无法纳入个体自由,因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被视为某种空洞理想的谚语,本质上无非就是对希腊伦理本性所作出的解释,那么在对渗透到伦理本性里的更深原则的意识中,这个原则在伦理本性上直接地还只能作为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渴望,从而只能作为一个腐败的东西表现出来。柏拉图正是出于这种渴望,不得不寻求援助来对抗这种腐败,但必须要从高处而来的援助,首先只能到希腊伦理的一种外部的特殊形式中去寻找,他心想借助于这种形式就可以克服那种腐败,殊不知经他这么做,恰恰把伦理性更深层的冲动,即自由的无限人格,损害的最深”。到了希腊化时代,城邦伦理解体,无限的自由人格这种主观自由再次成为哲学的主导原则,怀疑论、犬儒主义和斯多亚主义都表达出以强烈的主观自由反抗习俗的伦理,但最终主观的自由让位于“自然”,“遵从自然而生活”成为斯多亚派的道德。只有通过罗马法私人财产权的确立,意志自由才第一次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定在”,通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主观的个体的自由意识才在现代哲学中确立起来,成为现代的伦理原则。

但是,黑格尔通过对近代自然法学派的研究,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反思,更多地发现了“自由主义者”们在确立个人自由原则以实现现代性的规范秩序时的失误,这就是依然是以个体自由的道德意识,即单纯的意志自由作为基石,而没有发现一种真正具有社会历史现实性的自由的规范秩序,是不可能单纯依据道德性的主观形式自由的,它必须通过政治制度化的正义为优先原则以构成一个伦理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因为政治制度化了的正义,是伦理性自由而非道德性的自由。因为“政治”是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正义是保障共同体内部每一个个体自由成为现实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个体主观意志自由的道德原则。这是黑格尔区别于所有以“原子化的个体意志自由”为基础构建现代规范秩序的关键之处。当然一提到“政治共同体”,现在有人立刻就把它与“总体性”“专制”“极权”联系起来,它需要得到黑格尔式的理解,就得理解黑格尔的“伦理性”与共同体之间的生命原则,它确实需要艰苦的哲学论证,在这里,我只能把他思想的结论与要点表述如下。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由单个的具有主体性人格的自由个人构成的,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康德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理解没有差别,黑格尔也是坚持这一点的,但是如果立足于原子化的单个人的意志自由为起点,黑格尔则不同意,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知性的抽象,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原子化的个人,就像单个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样,单纯的个人意志自由也只是我们思考道德基础时,必须要有的一个先验设定,以便确立一个可以承担道德上赞美与谴责的责任主体。真正现实的道德自由,像康德所论证的那样,依然要考虑“意志的伦理性”,即你自愿意志的行动准则是否能够得到像你一样的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任意,如果不能,那么你的主观自由之意志依然是不自由的,无法成为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只有你在主观反思的“形式上”达到了意志的伦理性,主观意志的行动准则才是有效的,因而一个真正的基于主观自由的道德原则之证成,需要一个形式主义的“意志的伦理性”共同体。这就是康德的道德立法力主形式主义立法原理且有一个“目的王国”之预设的原因。
所以,道德上的单一原子化的个体意志自由离开了“意志的伦理性”不可能真正存在,那么从原子化的个人自由来构建政治伦理共同体的正义就更成问题了。我们依然以康德为例来说明。康德通过法权论来建构其基于个人意志自由的规范秩序,先从权利上区分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这没有问题,明确区分了“我的”和“你的”权利边界,使得我们的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从而得以实现,这是自从罗马法以来的传统。黑格尔也同意这一点,通过私有财产权的确立获得个人意志自由在法权上的“定在”形式。但法权的实现,不是有一个抽象法的规定就完成了,其真实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规范秩序,个人自由只是这个规范秩序具有正当性的先验基础,而不是已经实现了自由权利本身。法律规定了的权利仅仅是字面上的,其真正实现必须有一个真正承认法律价值、遵守法治精神、敬天守则的伦理共同体,才能以法律所规定的规范与秩序确立自己的职权边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才能实现。
所以,康德在“法权论”上阐明的法权或正当概念,不是单就个人的意志自由来确立,而是就每一个人主观的意志自由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自由如何能够共存来确立:“任何行为若能根据一项普遍法则而与每个人的自由共存,或是依据该行为的准则,任何人所意愿的自由能根据一项普遍法则而与每个人的自由相共存,这个行为便是正当的(recht)。”此“正当”就是“正义”。这里的自由就是个人行动的外部自由,康德强调了行为“正当性”的三个要件:每一个人自己所意愿的自由,根据一项普遍法则,与每一个其他人的同样的外部自由能够共存。因此,自由的边界就是自由之共存的可能性,即任何人自己所意念的自由没有任何理由损害他人意念的自由的权利,相反,必须根据一项普遍原则与每个人其他人所意念的自由相共存。于是,法权论上的自由之实现也就必须是在“伦理关系”中才是现实的,这种伦理关系意味两点: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之自由的共存性关系和这种关系是靠每一个人都能自愿遵守的普遍原则来维系的。任何符合这两点的伦理关系都是自由的,而不是强制的或专制的。所以,康德也论证了,哪怕是我们对外在物品的占有权,虽然意志自由是合法占有的基础,但是,“唯有在一个公民组织中,某物才能终极地被取得;反之,在自然状态中,该物固然也能被取得,但只是暂时地被取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任何单个的意愿和个人自由,要真正获得实现,就必须是在某种伦理关系中,这也就是黑格尔反对康德的道德性立场而要进展到伦理性立场的关键原因。
康德等主观性哲学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单个人如何构成一个具有伦理性的社会共同体问题上,采取了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这是黑格尔所不能同意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黑格尔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契约论,在单一法权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上,黑格尔依然是认同契约论的,但是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等伦理实体,黑格尔则坚决反对近代以来的契约论解释。

原因有三:其一,说家庭完全是契约关系,就把家庭真实的伦理意蕴给取消了,家庭之成立首先依据的是男女双方之间的爱情,其次才是法律契约,再次是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亲之爱的相互义务,契约仅仅只是家庭合法性的一种外在法律形式,契约可以缔结也可以废除,但家庭之间的血亲之爱,一旦产生就永久不变;其二,说国家是由契约产生,根本就是不顾历史现实的抽象假定,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根本不需要这种假定;其三,任何依据契约产生的共同体都只是原子式个体之间的一种外部联合,因此,只能达到一时的脆弱的外在联合形式,不能形成一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的有机体。因此,真正的现代性自由的规范秩序,在黑格尔看来,就要放弃自由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单一自由个体通过契约来外部联合的做法,而要通过伦理精神的“活的善”来构建伦理实体的内在有机体,才能真正实现自由的规范秩序。
通过内在的伦理精神而不是外在的法律契约为什么就能真正构成一个真实的政治—伦理共同体而不重蹈专制城邦的覆辙?因为精神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构成性力量,它源自古希腊的“灵魂”概念,在1804-1805年的《耶拿体系草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中,黑格尔就把“灵魂”视为“一种把诸要素独自地、绝对被分离开的综合”力量,“一种交互作用的漠不相干的在完全一致中的综合”,透过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术语,黑格尔要说的是,“灵魂”是一个实体之成为一体的根据,或者说是这个根据本身的实存,这个根据本身并不脱离实存物,实存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实存物,因为它有灵魂,灵魂成就其实体之为实体。更进一步说,一个实体如果没有灵魂,就是一些漠不相干的“诸要素”,独立的、不相干的、绝对被分离开的东西,不成为一物,没有一体之生命,而有了灵魂(气息),这些不相干的“诸要素”就有了“交互作用”并有了生命之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体之物。所以,后来黑格尔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论述了“精神与有机体”。
一个有机体是由各种成分或要素构成的,但各种成分或要素不会自动地交互作用,靠什么把各种要素或成分组合成为一个有机体呢?就是靠“精神”。因此,精神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因为有机体有“精神”,才有有机体之生命。精神于是就是内在的生命原则。生命作为有机体,意味着生命能把诸多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内在的交互作用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部分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每一个组成要素都是一体生命的前提,可以独立存在,可以“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功能,但在整体中又没有一个部分或要素是多余的,每一个独立成分的损坏都可导致整体生命的死亡。因此,伦理精神就是这样一种把所有单一的自由个体组成一个伦理共同体或伦理实体的内在生命原理。
有了这样的伦理实体,现代的自由规范秩序才能真正地变成现实,才既不会因知性思维的外部主观反思导致恶的无限性,也不会因临时任意签订的契约之不可履行而随时让法律政治共同体陷入瓦解的危机。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寻找到了现代性自由的规范秩序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向。以此为基础,善的脆弱性、文明的脆弱性危机,都可以寻到解决的方向与路径。
因此,在当前世界处在极不确定的无常而茫然无措时,黑格尔依然是我们的导师,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与领会。这就是我们《伦理学术》第9期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探讨核心的缘由。由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国内研究成果较少,目前只有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和杨祖陶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对《精神哲学》中的“人类学”部分的研究国内尤其缺乏,因此我们特别翻译了德国当前相关研究专家的论文,应该说,对推动我们对《精神哲学》深入理解将大有裨益。至于黑格尔法哲学研究,规范秩序的建构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重点,本期也在深化讨论的内容。
关于美德伦理学的讨论,本期推出了黄勇教授、郑开教授的重头文章,非常值得关注。刘畅和朱锦良博士翻译的瓦登菲斯的《响应伦理学:在回应与责任之间》是一种新的伦理学纲领,推进了我们对于“责任伦理”的理解。尚杰教授的《差异不同于存在——私密的自由》和张念教授翻译德里达的《性差异:存在论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法国哲学的新思想。在“描述伦理学”栏目下,唐瑞和倪胜教授翻译的《马丁麦克多纳的<枕头人>,或为文学辩护》和《友谊与雅斯米娜雷扎的<艺术>》以新的视角阐释了伦理叙事中的文学与艺术的意义。本期还在人类学视野下,继续探讨关于动物伦理、儿童哲学和黑格尔有关“灵魂疾病”“疯狂”等伦理生活中的重要现实问题。
感谢所有作者和译者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们在无常与不知所措的今日世界共同守护伦理精神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