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简<五行>章句讲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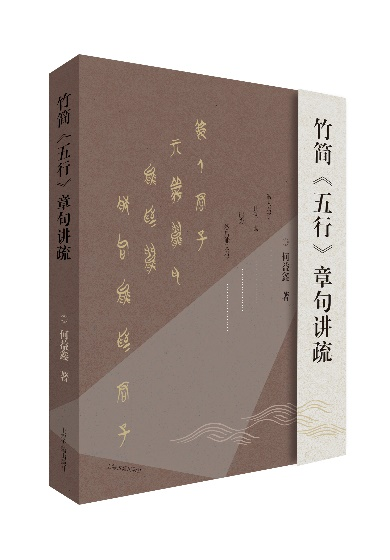
作者:何益鑫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郭店竹简《五行》作为思孟学派的核心文本,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出土、公布以来,诸多学者时贤围绕《五行》做了大量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早期儒学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线索为基本的理解背景,通过逐字、逐句、逐章的分析讨论,重新论定《五行》的内在旨趣、行文思路和思想要义。与前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一样,本书也采取了“章句-讲疏”的写作形式,以“导论”为纲领,以“章句”为根本,以“讲疏”尽其义。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家哲学、早期易学。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等。获评2019年第八届“士恒青年学者”,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新锐奖”(2023年)。
导论:德的生成——子思《五行》篇的德行生成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1
《五行》章句 1
《五行》讲疏 21
一、总纲 38
二、由仁而智圣以至于和 59
三、由圣智而仁以至于和 167
四、余论 283
引用文献 291
后记 297
* 出于编辑需要,章节选读部分注释被省略,详情请参见原文
圣之思也轻,圣之思,谓圣之行于心术者。圣者,智之极。轻,快也、易也。言神思悠然、倏忽而至,犹“不思而得”也。轻非不长,以其流行之易,不假用力,若无为而然者也。○《荀子·不苟》:“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言操之熟乃轻耳。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聪者,圣之藏于耳也。闻君子道,谓能于众中辨识之也。更知其所以为君子道,知其为天之道,则玉音。玉音,犹德音,有德者之言也。至于玉音,则圣德成矣。
右第七章。言圣之思也,至于玉音而圣成。
本章是讲从“圣之思”到“圣”的成形过程。圣从属于广义上的智,与上章所说的智有关系,又有区分。
第一句“圣之思也轻”。与前两章相似,“圣之思”指承载了圣的意识活动,或者说圣德在意识活动层面的载体。它的基本特征是“轻”。那么,什么是轻呢?帛书《说》解释说:“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魏启鹏说:“‘轻’有轻举,飞升和上扬、超越等含义。故帛书《五行》之帛书《说》得以‘轻者尚(上)矣’解诂。”常森说:“殆谓思考天道或者德臻于精熟之地就超出常人。尚,超越,高出;《论语·里仁》篇载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轻举、超越、高出,都是与上下方位有关。要注意的是,一如仁之思的“清”、智之思的“长”一样,“轻”乃是“圣之思”的特征,而不应该是指向圣之思的对象。且从上下文看,对象的凸显至少要到“聪”的阶段之后。故帛书《说》“思天”的解法,与简文本义未必相契。又,陈来先生认为:“轻本是指声音的轻细而言,圣就是对声音有敏感的听觉的人,圣表示对再轻细的声音也能听到。”与前解不同,这是从“圣”与“聪”的关系入手。不过,与前解类似的是,此说中的“轻”也是形容圣之思的对象(声音轻细),而不是圣之思本身的活动特征。
庞朴先生指出:“《礼记·中庸》所谓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及《荀子·不苟》‘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可作“圣之思也轻”之解。”相对而言,这一解释直接以《中庸》和《荀子》为依据,其对轻的了解更为可靠。
故此,圣之思的“轻”,不是由于思的对象的差别,而是关乎思的精熟程度。思之轻,可以是相对于思之重而言。思之重,是费力思考而得的;思之轻,则是“不思而得”。《中庸》所谓“不思而得”,即圣之思也轻;与之相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得,便是人之思也重。《荀子·不苟》所谓“操之”,是用心操持,思之重者也;“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得之而独行之后,思之轻者也。伊川答横渠曰:“所论大概,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答横渠先生书》)这一说法也可以借以说明问题。伊川说横渠的论说,多是苦心极力的考索,是思之重者;而与之相对,来源于“明睿所照”的自然见解,则是思之轻者。
因此,思之重或思之轻的差别,主要不在内容,而在思维的过程:费力或不费力,有迹或无迹,有意或无意。如果说,智之思的“得”,必须经过“长”的阶段,亦即经过一个在时间中持续的思维运作的过程;那么,“圣之思也轻”,似乎是指不需要时间过程的直接的把握,近似于一种理智上的直观。其实,可能并不是真的直观,只是其思维的过程隐没在了结果的瞬间呈现之中,只是作为此结果的一个内在结构而存在。而这一过程本身,在思者本人这里,甚至都没有进入到自觉的意识状态,故有一种不期然的、无意的、不思而得的体验。
接着是“轻则形”。这里的“形”,显然要与“形则圣”相区分,它不能理解为德之行的成形。那么,这个“形”是什么意思?学者基本上没有给出有效的解释。所幸的是,从本章开始,帛书就有对应的帛书《说》内容了。关于这一句,它有很多的发挥。
“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下子轻思于翟,路人如斩。酉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形也。
把“圣之思也轻”从内容上解释为“思天”,未必是对此句最有针对性的、最直接的解释,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不过,帛书《说》对“轻则形”的解释很值得参考。“形”即“形其所思”,举了一个酉下子的例子。这里的“酉下子”,一般认为是柳下惠。《论语》有三章(四次)提到他,《孟子》则有五处(六次)提到他,并称他是“圣之和者”。但此处的故事,却不是很好理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何谓“路人如斩”、“路人如流”?整理者指出:“斩流皆喻行止之态,《商君书·赏刑》述晋文公将明刑以亲百姓,‘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此说可从。所谓“路人如斩”,说的是路人好像被砍了脚一样一动不动;所谓“路人如流”,说的是路人行走穿梭没有停顿。
何谓“轻思于翟”?魏启鹏说:“於翟,当与《四行》所谓‘其事化翟’义同,‘於’,鱼部影母。‘化’,歌部晓母。其韵鱼歌通转,古所常见;影、晓古为喉音清声旁纽,其声同类,故‘於’之与‘化’音近。……‘於翟’同‘化翟’,化施变易也。”所谓《四行》,指帛书《五行》经说之后的一个文本,有人认为是《五行》的后叙。其中有这样的说法:“圣者知,圣之知知天,其事化翟。”魏启鹏解释说:“化翟通‘化易’。……《荀子·君子》:‘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谓变化移易也。《孟子·尽心上》:‘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哉!’《尽心下》:‘大而化之之谓圣。’可与‘其事化翟’之意互相发明。”参照魏氏的解法,则此处“轻思於翟”可以理解为,柳下惠的轻思已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那么,串起来又怎么说?由于柳下惠是“士师”(狱官),故整理者认为:“路人读为累人,指系囚。”顺此,魏启鹏说:“路人如斩,谓累人皆从柳下惠之断狱也。……路人如流,即谓累人亦从柳下惠之刑德教化也。”这一说法似乎不妥。即便“路人如斩”和“路人如流”可以这样解释,问题是,这与“酉下子轻思於翟”有什么关系?与“形其所思也”又是什么关系?“酉下子见其如斩也”,为何要强调是柳下惠的“见”?说的还不够圆满。
常森认为,这句话“殆谓柳下惠精熟地思考于翟而忘怀其他,以至于认为行走的路人像被斩去脚一样静止,——这只是柳下子见路人被斩去脚一样静止,路人其实像流水一样在行走。句意是说对对象的高度集中,超越了对其他事物的关注。”此说除了把“翟”解作鸟,认为柳下惠是在专心思考鸟的问题,这一点令人费解之外,大体还是抓住了一些要害的。“路人如斩”,不是真的路人如斩,而是柳下惠思中所见、见其如斩;真实的情况,却是“路人如流”,路人从来没有因为柳下惠的思,而停止过穿行的活动。常森说,这句话的主旨是突出柳下惠由于思考高度集中,超越了对其它事物的关注。这一解释,无法落实“形”的意义。从原文看,“形”无疑是此中的核心概念。帛书《说》“言其思之形也”,在语脉中是作为故事的总结。这表明,柳下惠的例子,所谓“路人如斩”、“路人如流”,最终都是为了说明“形”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形”与“见其如斩”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此中的突破口,是“路人如流”的事实与柳下惠“路人如斩”的所见,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柳下惠之思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现实中路人穿行在他的世界中,就都好像停止了一样,定格在那里。这样的思,实是一种直观的、整体的把握能力。我们一般对于事物的观看和了解,总是有一个顺序的,从一点到另一点,从局部细节的观察开始渐渐形成整体的把握,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对于静止的事物,尚且这样;对于运动的事物,更加如此。事物如果运动过快,很可能在我们对它形成整体的把握之前,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在这个故事中,川流不息的人群正是运动的事物。对它的观察,普通人只能抓住其中的部分细节(比如看到了其中有一个奇装异服的人,或者看到一个异族人,或者夹杂着一个闹哄哄的小孩),即便给你时间不断地观察,也是很难形成完整的把握,看清楚全貌的。因为它一直在动,动意味着新状况的不断出现,具体的事态稍纵即逝;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它、思考它的过程都是需要时间的,几乎不可能把握某一个特定时刻的整全面貌。然而,对于柳下惠来说,流变中的事物,看上去是静止不动的。不是说真的静止不动,或者柳下惠有时间定格的能力,它其实是说柳下惠可以在每一时刻没有错漏地同时把握路人的全部事态。当然,本质上,这种能力取决于柳下惠具有的超强直观和综合把握的能力。帛书作者认为,这是柳下惠“圣之思”出神入化的表现。
电影《头文字D》里面讲到一个现象,拓海在秋名山上送豆腐,一年又一年,他发现周围的世界在渐渐变慢,而实际上,是他的车开的越来越快。拓海为什么会觉得世界很慢?因为尽在他的下意识的掌控之中,不需要有意识的思考就可以操控,没有新的情况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活动。与之相反的是,当我们刚开始驾车的时候,觉得道路上的事态变化的好快。为什么会觉得快?因为对于新手而言,每一种路况都是经过观察-思考-操控的这一复杂的过程而实现的。且对交通事态的观察,又是一个点一个点,通过注意力的持续转移而拼凑出来的。所以总是会觉得,路况更新太快,要注意的点太多,一个脑子不够用。设想,如果大部分的路况都很熟悉了,都在下意识的反应之中,那么,脑子就会留下足够的时间,让你处理可能偶然发生的新情况。进一步,如果一切都是熟悉的路况,通过肌肉的习惯性记忆就可以应对,那么,此时就会觉得整个过程是不需要意识活动参与的,只要一瞟就能洞悉全局。在此一瞟之中,时间近乎是停止的,因为它几乎已经不需要在意识层面的接受和综合的时间了。拓海达到的是第二重境界,时间慢下来,但还没有停止。他只是熟悉了那条秋名山的盘山路,若换成其它地方的路,他还是需要经历一个渐渐熟悉、渐渐自如,以便让时间渐渐慢下来的过程。而柳下惠达到了第三重境界,他对事物的观察和理解近乎直观,瞬间把握全局。似乎世界对他来说可以随时停止,就像照相一样,待人细细回顾其中的细节。
帛书《说》为什么会举“路人如斩”的例子呢?这倒确实可能与柳下惠的士师身份有关。士师断狱,最重要的是细节的观察和把握。或许柳下惠非常善于把握事态与细节,只要一过目,悉在掌握之中。故帛书《说》作者以他为“轻思化易”的代表。
如果进一步打开脑洞,柳下惠见“路人如斩”的例子,似乎也可以从比喻的角度说。“路人如流”指一般的思的活动,它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历时性运思的过程,其结果要在进程全部完成之后才能呈现。相对而言,“路人如斩”指一种无时间性的直观把握,思的始与终一时呈现,没有了思的过程。由于思路急速铺开,以至于感受不到意识活动的时间性,则思者最终的感受只是刹那获得、瞬间完成,此则《中庸》所谓“不思而得”。但它不是没有头绪的孤零零的一个终点,若要反思其思路之所由,又可以历历在目地呈现。换言之,圣的不思而得,其实不只是一个结果,更是可以“直观”从思路到结果的全体。一个本来要在意识活动的历时过程中逐步展开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在空间中平面铺开、直观可见的东西。就好像不断发生变化着的穿梭的人流,定格为一幅静止的画面。平铺的东西,可以同时直观到全体,这就是“形其所思”(历时过程图像化)。故“形者,形其所思也”,形就是“所思”在“思”中的呈现方式。这个意义上的形,与《乐记》“心术形焉”的“形”接近。
以上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与帛书《说》的原文更加贴切,可能更加接近帛书《说》作者的用意。顺此,这一句中“形”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圣之思对于事物或者对象的把握方式。智之思要经过一个历时性的复杂的运思过程才能“得”,这个“得”指的是对于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故曰“长则得”;与之相比,圣之思对于对象的理解是近瞬间达到、近乎直观的,不需要意识活动的过程,非常轻易的,故曰“轻则形”。当然,“长则得”也可以理解的很深,故此处“得”与“形”并不强调内容的差别,而是凸出了过程的区分。得强调结果,形强调综观,基本意义是一样的。
得之后,都不会忘记,故曰“形则不忘”。智的不忘,是因为新事物在既有的意义脉络和知识背景中获得了理解,得到了条理化、系统化的整合。圣的不忘,说到底也是由于内部的一贯性,只是它的一贯性更为圆融和无迹。故对新知识的接受,无需理解和运思的过程,自然融入。
在此,帛书《说》云:“‘形则不忘’。不忘者,不忘其所□也,圣之结于心者也。” 根据上下文,缺字当补为形。圣之思的活动,对于事物而言也是一种表象活动。故“所形”是指圣之思所表象的对象,或者说是圣之思对对象的表象结果。这种表象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呈现活动,更是一种理解活动。所以,“不忘其所形”,意思就是不忘记对事物发生过的理解。
而这种能力,从根源上源于内心既有的圣德,从结果上它的积淀又反哺了后者,构成了下一次的圣之思的活动的基础,故曰:“圣之结于心者也。” 结,谓缔结、凝聚。一般而言,圣的意义,与卓越的听觉能力相关。但圣聪,不仅仅是感知的能力,更是认知和理解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是要以学者内心的义理体段为前提的。故圣之思之所以轻,源于义理之精熟;形则不忘的结果,又反过来充实之,两者互为因果。这一点与智是相似的。池田知久认为:“此句是讲,在人类的‘心’中先天地自然地被赋予的‘圣’,是‘思’、‘形’这样一种后天的人为的努力的结果,再返回本来的样子,成为‘结于心’而‘不忘’的状态。”按,在《五行》中,圣或许有天生的因素,却不是一种完全天生的德性。所以,才会有圣这种德之行的形成问题。圣的形成,或者说它在内心的凝聚,源于圣之思的意识活动。这个活动是人为的,但又不像是人为的,因为它似乎是直观的、自然的,淡化了“人为的努力”。由圣之思自然而然的活动,得到新的理解反哺、积淀于内心,成为下一次圣之思的基础,如此反复,则圣之思越发的轻,越发不思而得,这便是“圣之结于心”的过程。
以上是圣之思的内在活动,尚未涉及到感官功能。接下来是表现于外的实现活动,依托于感官。
“不忘则聪”。儒家之前,圣、听、聪三者已有稳定的关联。庞朴先生说:“《书·洪范》:‘听曰聪。’古佚书《德圣》:‘圣者,声也。……其谓之圣者,取诸声也。’《文子》:‘闻而知之,圣也。’(定县汉简1993)《白虎通·圣人》:‘圣者,声也。……闻声知情。’又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畋游》:‘故听、声、圣乃一字。其字即作𦔻,从口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动作则为听。圣、声、听均后起之字也。圣从𦔻壬声,仅于𦔻之初文符以声符而已。’”实际上,诸说关于圣、听关联的论述,需要作出层次的区分。第一层意义上的圣,与听觉敏锐相关,“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能力和素质”,如郭沫若所说;第二层意义上的圣则是作为德行的圣,如帛书《德圣》(魏启鹏命名为《四行》)、《文子》等所说。作为“德之行”的圣,无疑是后一种。
故帛书《说》云:“‘不忘则聪’。聪者,圣之藏于耳者也。犹孔子之闻轻者之击而得夏之卢也。”聪是“圣之藏于耳者”,也就是说,聪是圣在听觉器官上的表现。在这一逻辑中,聪不是独立的能力,它取决于内在的圣。结合“不忘者……圣之结于心者也”的解释,则“不忘则聪”是说以结于内的圣心为前提,然后有聪。故此处的聪,就不仅仅是一种敏锐的听觉能力了,而是以内在心德为基础的“听觉-分辨力”。
帛书《说》的后半句,出典未详。有三种猜测。整理者说,轻读为磬,盧读为虡,是悬磬的架子。意思是说,孔子听人击磬就知道架子是夏朝的架子。庞朴说,轻者疑轻吕之误,轻吕,剑名。夏之卢或为夏启剑。意思是说,孔子之闻轻吕之击而得夏之卢。魏启鹏说,夏之卢即夏之搏,搏之声也轻微。孔子闻轻者之击而得夏之搏,殆寄其向往有夏,推崇大禹之意。三者都不能在传世文献找到典故出处,但相较而言,第一种可能更为合理。
《晏子春秋》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景公为大钟,将悬之。晏子、仲尼、柏常骞三人朝,俱曰:‘钟将毁。’冲之,果毁。公召三子而者问之。晏子对曰:‘钟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礼,是以曰钟将毁。’仲尼曰:‘钟大而悬下,冲之其气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钟将毁。’柏常骞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胜于雷,是以曰钟将毁也。’”这一则记载很可能出于后人的演绎。但就这一记载而言,孔子从大钟悬挂的位置,推论回声容易使钟发生过渡震荡(共振),从而推定了此钟将毁。但问题是,一个钟的共振频率取决于很多条件,除了悬挂高度之外还与自身的厚度、大小有关。若果有其事,更有可能是孔子已经听出了钟声中的共振,从而作出了这一判断。后来在钟的频繁使用中,果然毁坏了。这就取决于孔子音乐听觉的敏锐,以及乐理的精通。
如果以上事件是可能的,那么,通过击磬的声音而判定架子的年代也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架子,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其年代的特殊性:其一,架子的型制,不同的年代架子的规制或有不同;其二,所用木材,不同年代惯用的木材可能不同;其三,年代不同导致木材的物理性质(如干湿度)和声音特质(共振频率)发生变化,这一点只要从斫琴的用料选择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四,架子上的勒痕深度,改变了磬与架子的接触面和接触程度,也会影响音质。这四者的差异,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在击磬的音质上。综合以上因素,至少从理论上,是可以从击磬的音质而判定架子的朝代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就如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出一把古琴用的是老料还是新料),但孔子无疑有这种能力。故帛书《说》举了这个例子来说明“聪”。
下一句“聪则闻君子道。”以上对“聪”的解释,还没有特别凸显道德的意义,此句揭示了这一点。本章的“聪”,可以包含宽泛的含义,但主要还是指向道德上的识别、理解和判断力。故所谓“闻君子道”,不只是听闻君子的学说而已,更主要的是听了之后能够识别出“这是君子道”;并且知道君子道何以为君子道之故,所谓“闻君子道而知其为君子道也”。换个角度说,听到的人可能很多,但唯有圣之思发展到这一步的人,才能真正识别出君子道、理解君子道之为君子道。这就绝不是感官听觉的问题了,跟是意味着道德上的敏锐、洞察、理解和判断。
帛书《说》解释说:“道者,天道也,闻君子道之志耳而知之也。”志,记忆。知,理解。本章简文只是说“君子道”,帛书《说》则直接以天道解之。其实,君子道在这里应是指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之道。《五行》作者(子思)认为,儒家的道是合乎天道的,或者说是与天道相通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道者,天道也”;就如《五行》第1章“德,天道也”,也主要是从两者境界的相通性而言的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君子道与天道是完全等同的,适当的区分还是必要的。根据第17章的表述,圣人确实是“知天道”的。不过,这里的关键在于,圣人所知的,作为指令的发出者或规范性的最终根据的“天道”,与以儒家学说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君子道”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想,就子思而言,他对天道的领会、对圣人的领会,以及天道与君子道的一致性的了解,最明显表现在《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以及相关表述中,比如: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所谓“天之所以为天”,也就是天道之为天道的本质,在于“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文王之所以为文”,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在于“纯亦不已”。两者是内在一致的、相通的。君子道之为君子道与天道之为天道的一致性,意味着对君子道之为君子道的认知,实际上包含了对天道之为天道的确认。在此意义上,知君子道之为君子道,也就是一种意义上的确认天道、知天道。因此,《五行》所谓“圣人知天道”,或许主要是通过君子道的理解而透显天道的本真,而不是由特异的听觉能力接收来自上帝的声音。
接下来“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原指玉磬之音。第9、10章说提到“金声而玉振之”,古乐必始于金声,终于玉音,以玉音能收之故。此处,“玉音”是说圣人之“天音”。魏启鹏说:“简文之玉音,犹德音也。盖《五行》篇以德为天道,知天道为圣,又以‘玉音,圣也’。故知玉音乃象征知天道者、有德者之音。参看《国语·周语下》载伶周鸠曰:‘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韦注:‘中德,中庸之德声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人以宁,民是以听。’又,《国语·楚语上》:‘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心类德音,(韦注:‘类,善也。’)以德有国。’”在《诗经》中,“德音”出现了12次。郑玄有“恩意之声”“教令”“声名”“先王道德之教”等不同解法。在《礼记》《荀子》及汉人文献中,玉音一词也经常出现。如“其德音足以化之”(《荀子·富国》)、“厚德音以先之”(《王霸》)等。本章的 “玉音”,与闻君子道有关。且从“玉音则圣”看,这一阶段意味着圣德的完成。故这里的“玉音”,应是指圣人之言,或出于圣德的言语。
关于这一句,帛书《说》解释说:“‘闻君子道则玉音。’□□□□□□□而美者也,圣者闻志耳而知其所以为□者也。”后一个缺字,整理者释为“物”。池田知久参照帛书《说》“见贤人而不色然,不知其所以为之”,补“之”字,指君子道。可从。前面的缺文也有争议。池田知久据后文“□□也者,己有弗为而美者也”,补“玉音者己有弗为”,应该是不合适的。彼处“己有弗为而美”是形容德的,而本章即便到了“玉音”,与德的完全实现还是不同的。这句话,虽然不知道怎么精确地补充,大义还是清楚的。既然说是“玉音”,则阙文一句应当是说圣者出言之美。至于为何能出德美之言,是因为圣者听闻、记住了君子道,并且深切地理解了君子道之为君子道的原因,所谓“圣者闻志耳而知其所以为之者”。
从“圣之思也轻”开始,经历了“形”“不忘”“聪”“闻君子道”,到了“玉音”的阶段,说明圣之结于心已经完成,圣这种德之行已经内在成形,故曰“玉音则圣”。
从以上两章来看,智与圣虽然都属于广义的智,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基本的不同是,智之思是长,圣之思是轻。前者是历时性的、过程性的;后者几乎是瞬间达到、近乎直观的。从对象或内容说,智的主要任务是识别贤人,理解贤人之为贤人的德;圣的主要任务是识别道,理解君子道之为君子道,并且契会和确证天道。比较智与圣的形成过程,在“不忘”以前,都是内在的运思、理解、记忆活动,此后才区分为“明-见贤人”或“聪-闻君子道”。同样都是理智德性,为何会联结到不同的感官?又何以要建立对象的区分?智难道就不能有听觉的参与,并且无法了解君子道了吗?圣难道就不能有视觉参与,并且无法鉴别贤人了吗?事实上,对于贤人的了解和识别,不仅仅是通过视觉,更要依据他的言谈。所以,“明则见贤人”的见,其实不能具象地理解为视觉上的看见。同样的,对于君子道的认知,也不仅仅是听觉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文本的阅读乃至圣贤的示范。所以,“聪则闻君子道”的闻,也不能具象地理解为视觉上的看见。
当然,明与智,聪与圣,在先秦时代的一般的了解中就有亲缘的关系。不过,我想问的是,除了这一层因素之外,《五行》把智、圣分别对应到见、闻两种感官,是否还有思想的必然性?
有两个方向或许是值得考虑的:一是认知的方式,二是认知的难度。从认知方式来讲,见的对象是有形的,闻的对象是无形的。理解贤人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察、交流和思考,由感性的把握渐渐上升到理性的理解。理解君子道,唯有借助于声音和文字(文字也要讲出来或读出来,根本上还是声音),没有其它可视化的途径。声音和文字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历时性。信息的接收是历时的,接收之后再领会意义,又是一个复杂的抽象思考的过程。圣的不同在于,对声音的接受及意义的领会是瞬时发生的,不需要过程和时间。它可以达到一种“意义的直观”。好像一个历时性发生的东西,瞬时平铺开来,以一种可视化的形式(意义图像,时间的空间化)得到了把握。帛书所举的“酉下子见路人如斩”的例子,就说明了圣者在表象活动中达到的意义直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孔子。子曰:“六十而耳顺。”(《为政》)耳顺,一般解为“声入心通”。“声入心通”,意味着声音与意义的瞬间转换。孔子可以当下领会声音的意义,不需要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任何的遮蔽。过程如此迅捷、彻底、且自然,这是孔子六十岁达到的境界。实际上,孔子还不只是“意义直观”,有时还会因意义的领会而表象为具体的形象。如孔子向师襄学琴,经过了“得其数”“得其志”的阶段之后,“(孔子)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学一首曲子,不但可以把握它的思想意趣,还能体会作者的生存意态和仪容风貌,并由此判定曲子的作者是文王。其判定,还被师襄子证实。可见,孔子的“闻而知之”,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以此反观《五行》,则“轻则形”的形,不仅仅是关于所思内容的意义直观,还可以包含意义的具象直观(人物化、情境化、图像化)。
无论是意义直观,还是意义的具象化,某种意义上都是向空间或视觉把握方式的转化。从人类的思维特性来讲,综合的把握(直观)往往具有空间化或视觉化的形式。因此,相较于“见而知之”,“闻而知之”多了一个抽象事物视觉化表象的环节。后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从认知难度来讲,有人真实地在你面前,言行举止各个方面都可以观察,可以与他有丰富的、立体的交流与互动(包括情感互动),理解起来当然容易一点;君子道是以语言和文本的方式表达的抽象的东西,理解起来当然困难。好比同样是文王,是文王身边的人更容易理解文王呢?还是千载之后的人,凭着关于文王的记载和传说,更容易理解文王呢?显然是前者。故下文第16章说:“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后来,孟子以“闻而知之”说汤、文王、孔子,以“见而知之”说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等(《尽心下》)。虽然不能说“禹”不是圣人,但相对而言,前一系列的人物更具有历史中继的意义。
要之,智更倾向于具象,故以“贤人”为对象,以“贤人之德”为理解的目标,此“贤人”可以说是道德的人格化的表现;圣更倾向于抽象,故以“君子道”为对象,以“君子道之为君子道”或“知其天之道也”(帛书《说》)为理解的目标,此“君子道”或“天道”乃是道德自身。具象以视觉为代表,抽象以听觉为代表。这或许就是《五行》作者将智、圣分别与明、聪对应的一个原因。具象的东西有其自身的边界,超出这个边界,智的运作就会很吃力。圣由于其思维的特殊性,能直接把握更为抽象的东西,或者说能透过具象事物而上达天道(知天道),这是智所不及的。《五行》把对于天道的理解以及境界上的契会,作为成德的最终阶段。有没有圣,也成为了“善,人道也”与“德,天道也”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