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实践哲学与德性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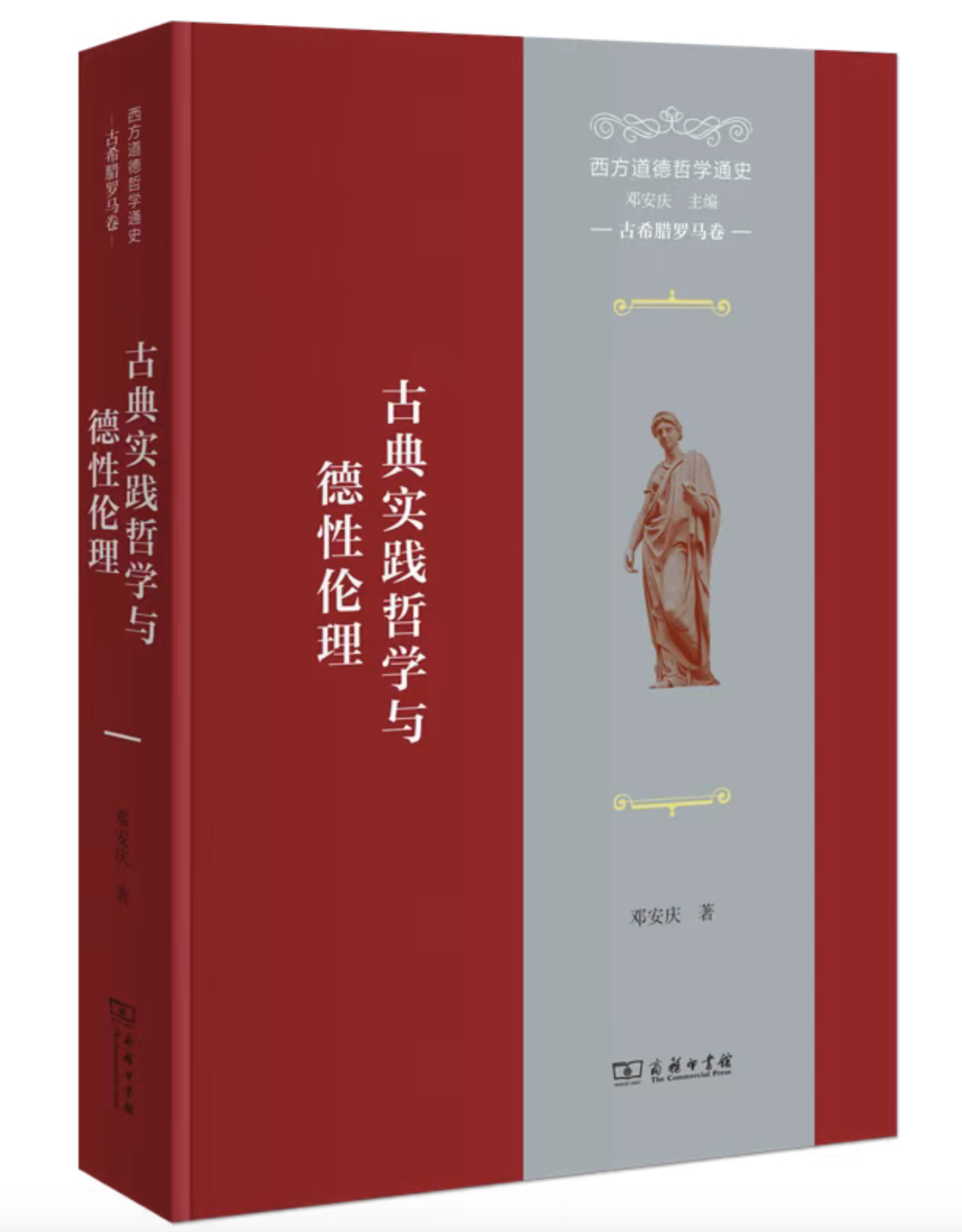
作者:邓安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月:2024年2月
简 介

目 录
导论 神话诗教、文明进程与古希腊伦理中的德性文脉
第一节 神话诗教
第二节 文明进程
第三节 “归家”本义
第四节 德性文脉
第一章 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中的伦理思想火花
第一节 “自然的逻各斯”与“存在之正义”
第二节 希腊本土自然哲学与伦理原则之萌芽
第三节 智者运动与古希腊人的德性教育
第二章 苏格拉底式伦理学定向
第一节 苏格拉底在何种意义上是西方伦理学之父?
第二节 伦理哲学核心命题之论证
第三节 灵魂的第二次航行:苏格拉底式伦理学之意义
第三章 前实践哲学的柏拉图伦理学
第一节 以伦理学为开端和归宿重构柏拉图哲学
第二节 作为“善本身”知识的柏拉图式“元伦理学”
第三节 城邦“共存”的正义伦理
第四节 生活中的爱欲伦理
第五节 依凭本性实存的自主德性论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与古典德性论的经典形态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三部伦理学著作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概念与方法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规范结构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伦理与德性论
第五节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伦理与德性论
第五章 希腊化时代哲学的重新定位:德性论伦理学的第二经典形态
第一节 “希腊化”与希腊化转向的源头
第二节 希腊化时代三大伦理学流派的思想定向
第三节 希腊化时代哲学的重新定位
第六章 伊壁鸠鲁主义伦理学
第一节 原子化的自然取代习俗化的城邦成为伦理学哲学的主题
第二节 对伊壁鸠鲁快乐主义的辩护性阐明
第三节 快乐主义的德性论
第七章 西塞罗的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
第一节 希腊哲学的拉丁化:由“伦理”向“道德”的转型
第二节 伦理生活中的“最高善”与“最大恶”
第三节 “得体”高于“知识”:实践哲学的“实用”转向
第四节 “政治”伦理高于个人“良心”:“共和国”及其“法律”的意义
第五节 德性论伦理学的义务论转向
第八章 塞涅卡:遵循自然与个人自由
第一节 哲学与人生
第二节 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伦理原则
第三节 如何能有个人生活的自由
第四节 作为个人心灵品质的德性论
第九章 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的伦理思想
第一节 爱比克泰德的个人自由伦理
第二节 奥勒留: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伦理与德性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词索引
导 论
神话诗教、文明进程与古希腊伦理中的德性文脉
伦理思想的源头是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塑造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意识的,是该民族的神话传说。即使到了雅典文明的高峰,到柏拉图对神话诗人的教化十分反感之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是明确承认神话诗教对他的影响:
我不得不明说,从小我就对荷马怀有喜爱与敬畏之心,让我不能违心地说他的不是。因为他毕竟是所有这些杰出的悲剧诗人的祖师爷和领袖,但是对我们而言,人不应该比真理赢得我们更高的尊敬。(《理想国》595b—c)[1]
这至少可以说明,当古希腊人真正懂得崇拜“真理”比崇敬“人”(哪怕是自己的祖先)更重要之前,《荷马史诗》的影响是空前的。神话不仅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且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认同的原型。因此,当我们开始研究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源头时,我们不得不探究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主要包括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Theogony)和《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每一个对欧洲历史或古典学感兴趣的人,都会有类似于历史学家曾经有过的这一惊叹:
这简直不可思议,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在欧洲郇窄的一隅,生活着近五百万陆地和海岛居民,他们拥有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却创造了最原始、最绚丽的文化、商业、社会秩序和政治……名闻遐迩。[2]
既不靠人口众多,也不靠地大物博,还没有令人感戴的皇家“仁爱”,区区五百万希腊人依靠他们的德性、宗教、制度和哲学,创造出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形态,让整个现代西方人,无不“言必称希腊”,哪怕历史的车轮来到了19世纪,站在欧洲哲学最高顶峰的黑格尔依然会真诚地承认,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德国,提起古希腊就会自然地涌起一种“家园感”。这确实是一种文化的尊严,文明的尊严,一种道义实存方式的伦理尊严。因为这种“家园感”不仅仅是多利亚柱式支撑起来的物质家园,那种家园早已随着历史的新陈代谢而灰飞烟灭,至多在艺术的废墟里残留了一些破碎的记忆,而是希腊伦理的家园,一种追求自由、美善、正义和友爱的伦理精神之家园,黑格尔将此精神称之为“美丽、自由的希腊伦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不断勾起现代人对于古老希腊文明的想象、记忆和不断复兴。但黑格尔同时说:
要是有人以为这样美丽和这样自由的生命,是由一个种族在血统关系和友谊关系范围内,经过了这种毫不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产生——这种观念实在是肤浅的愚昧。甚至于那最类似于这种沉静、和谐的展开的草木生命之所以能够生长,也完全靠了阳光、空气和水相互对峙的活动。“精神”能够有的那种真正的对峙是富于精神的;只有靠它本身的不同,才能够取得力量来实现它自己为精神。[3]
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描述,而是理解,不是“叙事”,而是思考这种伦理精神究竟从哪里取得养料和力量,在古希腊人艰苦卓绝的生存史中、在与各种异质精神的“对峙”中既确保本身的“不同”,又“实现它自己为精神”的。
黑格尔给予我们的一个善意提醒,就是不要在理解精神时陷入常人最常陷入的那种“肤浅的愚昧”:以为在一个单一种族的“血统关系和友谊关系”的仁心善念中,就能确立起伟大的伦理精神。无论是“伦理”还是“精神”,它们各自都需在异质元素的融合与分离中造就自身的存在,“融合”的条件是“共生”,而“分离”则是将不适合于“共生”的要素排除以达到“相生”。因此,“伦理精神”的目标是对内必须能够将不同“血统”的人、不同族群的人联合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使所有人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构成元素,在此共同体内获得其不可取代的位置和认同;对外必须能够在与“异质精神”的“对峙”中,理解和吸纳异质性精神以成为自身生命的养料,从而“保持”自身的“不同”,壮大自身的力量,成为所有人“安身立命”的“居所”。
因此,“伦理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同其他不同民族在生存斗争史中的“精神劳作”,其核心是以“道义实存”创造美好生活,因而伦理就在于把道义实存的伦理意识举而措之为礼法制度,从而让每个人能超越个人偏狭的自私与狭隘,确立起正义与友爱的和谐共存伦理关系,在此文明的伦理关系中以每个人自身的德性卓越活出每个人的幸福和荣耀。希腊文明的历史就是这种道义实存精神的发生发展,从而在哲学的思想中获得自觉的见证。我们从神话诗教、文明进程、“归家”本义和德性文脉四个方面展示古希腊伦理的“精神劳作”。
第一节 神话诗教
理解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早期历史,如果完全按照考古发现而不顾及其神话传说,其实都困难重重。雅典人宣称其为希腊的土著民族,但比其更早的是阿提卡(Attica)。在雅典人的信仰中,“这个国家的人民是阿提卡土地的后代”,“一般承认,在希腊历史发端之前,至少发生过一次来自北方的入侵,或许可以区分出前后相继的两般潮流”。第一波入侵的移民,被冠之以“伊奥尼亚人”(Ionians),在《荷马史诗》中雅典人被归为“伊奥尼亚人”。“后一波入侵者,一般被称之为多利安人。”[4]所以现在的历史学家将希腊的历史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但如今我们所知的最早文献记录——荷马的《伊利亚特》,涉及的是公元前13 世纪的希腊人及其文明。[5]
根据传说,Hellas(希腊)来源于Hellene(希腊人)。Hellen(赫楞)“是丢卡利翁(Deucalion )和皮拉(Pyrrha)的儿子,即希腊人的祖先,希腊一词即从他而来。根据古老的希腊神话,无数年以前,奥林波斯山上的大神宙斯(Ζεύς/Zeus)发洪水摧毁邪恶之界,丢卡利翁和皮拉是仅有的幸免于难的两个人,是他们生了赫楞。赫楞有三个儿子:多鲁斯(Dorus)、克苏索斯(Xuthus)、埃俄罗斯(Aeolus)。克苏索斯又生子伊翁(Ion)、阿开俄斯(Achaeus)。他们就是多利亚人、伊奥尼亚人和埃俄利亚人的祖先。丢卡利翁还有一个女儿,生了马其顿,他是马其顿人的祖先,所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是表兄弟。Hellenes是希腊人共用的自我称谓。[6]
所以在有基于考古学发现的“信史”之前,几乎每个民族都有由祖辈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它不仅是构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因而成为后世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且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伦理气质具有最大的塑造作用。希腊的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神人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一般民族神话会把神人视为两个“世界”的存在,但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相信,那些神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如同雅典人非常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雅典娜”(Athena)的后人一样,他们也非常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祖先很早很早以前,就是与神生活在一起的,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如此一来,虽然神话说的是诸神的故事,但他们却相信,“荷马的诗歌用难以匹敌的力量和强度展现了人类行为”[7]。因此,最初的伦理就是“神话”教化的结果。
神话(μῦθος/mythos)是叙述诸神的生平事迹的“传说”,而并非神所说的话,以荷马(大约公元前9世纪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代表;赫西俄德(大约公元前8世纪人)著有《神谱》,解说诸神的“谱系”,也即诸神的“来历”“来源”和关系,把早先来历不明、源头繁多的各种神的传说系统化、谱系化了。希腊古人认为最初的神是“大地之神”盖娅,她是从“混沌”诞生或她就是“混沌”。我国古人也有“盘古开天辟地”之说,但未说“开天辟地”之前何来“盘古”?如果再往前推,必定也要说是来自“混沌”,因为天地之初、宇宙鸿蒙。所谓“鸿蒙”也差不多就是“混沌”。希腊语“混沌”(Χάος/Chaos)之音“卡奥斯”就成为大地之神“盖娅”之“名”:
世间最初出现的是混沌(Chaos)和盖娅(Gaia,即大地),二者构成了万物生长的坚实基础;后来,阴雾迷漫的冥狱之神塔塔如斯(Tartarros)、诸神中最秀美的爱神厄洛斯(Eros)相继出现。厄洛斯酥软了众神和人们的四肢,制服了他们的神志。埃瑞玻斯(Erebos,黑暗)和黑夜诞生于混沌之中,二者相爱交配,怀孕生下了以太(Aither,清气)和白昼。盖娅首先产生了闪耀着繁星的乌拉诺斯(Ouranos,天空)来同她自己交配,并把自己团团围住,作为幸福诸神的永久的坚固住所。然后她产生了高山作为宁芙(Nymphs)女神在山林中生活的出没胜地……[8]
“无名”即为“混沌”,“有名,万物则始”,即始于“盖娅”,她即“大地”。于是,神的谱系也即将成为宇宙诞生的历史,因为“混沌”和“盖娅”二者构成了万物生长的坚实基础。但在古希腊神话中,宇宙万物的生长,被当作了神的谱系诞生的一个“伴生”现象,而且采取的是“拟人化”的形式。大地之神“盖娅”同时被赋予了“大地之母”的意蕴,“母”才能“生子”,才有“生生”关系。因此,希腊古人认为盖娅作为大地之母和大地之神,具有最为旺盛的“生殖力”,这是她最主要的特征。传说从她的“指缝”中,生出了乌拉诺斯,作为原始的天空之神,是“阳性”之物,却是为“阴”所生。在这种“生殖关系”中,不是先有“天”再生“地”,先有“阳”后生“阴”,而是相反,“阴”生“阳”之后,才有了大地与天空的“交合”,每一块大地上都有一片天空,像黏在皮肤上一样,这样的“交合”,使得“天”不像在我们《易经》中说的那样,天然地具有了“天尊”对于“地卑”的神圣主宰地位,“天尊地卑”不仅在古希腊神话中确立不起来,在后来具有科学性的原子论的自然哲学中就更无法确立了。他们把“天”视为“地母”“所生”之子,是“大地”的“受造物”,后来才作为盖娅之“夫”,实际上这样的“夫妇”都是大地之母所造。当然,他们作为两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天地的洪荒之力,也如《易经》所言,是原始的“生生”之力。但乌拉诺斯作为“天”,“天然地”就只躺在大地盖娅的怀抱中发泄“淫威”,“性欲”旺盛,除了与盖娅“生育”之外什么都不做,他简直只是“功能性”的,不是“主宰性”的,即使“天地交合”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生命体,“天父”也从来没有构成对地母的主宰性力量。
但凡神都是主宰,不过希腊神话强调的是神“各主一方”,这也像人世一样,是残酷“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结果。
最早主宰世界的神族,是提坦(Τιτάν)巨神,他们都是由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盖娅所生,被称为“大地之子”,六男六女,个个无惧天地,勇猛善战,是大地的“希望”所在。六个提坦男神是:欧申纳斯(大洋河流之神)、许珀里翁(飞越高空的太阳神)、克利俄斯、科俄斯、伊阿珀托斯、克洛诺斯(Κρόνος,是天、海、地、冥、时空之神)。六个提坦女神是:泰西斯(Τηθύς,荷马认为她是众神始母,是欧申纳斯之妻)、忒亚(光,光明神之母)、摩涅莫绪涅、福柏、瑞亚(Rhea,第二代神后)以及忒弥斯(Θέμις/Themis,她本来主司土地,后来因与奥林波斯神结合被认为主司法律与正义)。在他们中,克洛诺斯是盖娅所有子女中最小但最可怕的一个“弟弟”,不仅狡猾,而且善于计谋,于是大地之母借助于这个小儿子表达了她的“洪荒”不满和对乌拉诺斯的惩罚,传说是这样的:
由于盖娅厌烦了天空之神每天只知道黏在其身上(因为“天地未分”之故),不可分离地满足其性欲,于是与其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制订了一个极其狡诈的计划:在自己体内制作了一个弯刀状的东西,放在小克洛诺斯的手中,小克洛诺斯埋伏在他在母亲的肚子里,等待着乌拉诺斯跟其母交合,机会来了时,他断然将其亲生父亲的生殖器飞刀阉割,扔出了九霄云外。疼痛得巨吼一声的乌拉诺斯,轰然与大地盖娅分离,从此永远固定在宇宙的最高处,成为真正的“天空”,再也不能动弹。祂无限巨大的身躯,就分裂出具有无数天体的宇宙。而那个被儿子割断后抛飞出去的生殖器,依然带着其精血,飞溅在大地盖娅身上,使盖娅孕育出了怪物巨人族(Giants)、复仇三女神厄里尼厄斯(Erinyes)和白橡树三神女墨利埃(Melia)。还有传说,那个生殖器一直落到爱琴海中,掀起一阵巨浪,从海浪的泡沫中诞生了专司爱情与美的性欲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从此,男女交合不再像原始天地交合那样,只有必然的生殖欲,而同时伴随了自由情爱之美。
克洛诺斯因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从而推翻了父亲的地位而成为第二代神王。父亲乌拉诺斯也因此诅咒儿子,会像他一样被自己的孩子所推翻。克洛诺斯长大后与姐姐瑞亚结合,也生了许多孩子,但为了避免父王的诅咒应验,他竟将生出的每一个孩子都吞到自己的肚子里。但是,在瑞亚生了宙斯之后,盖娅却建议她,不要再让这个儿子被吃掉了。瑞亚用布裹住一块石头谎称这是新生的婴儿,克洛诺斯将石头一口吞下肚里,让宙斯逃过一劫,他被送到克洛诺斯的姐姐宁芙女神那里抚养长大。宁芙作为神话中“次要”的女神,不出现在神权统治的大争大斗中,而是作为出没于山林、原野、泉水、大海等地的“精灵”和“仙女”。大凡自然幻化出来的精灵,一般都有美艳动人的少女形象,能歌善舞,不会衰老或生病,但也会死去,这样更加凸显出宁芙生命的自由象征。由宁芙女神抚养未来宇宙之王宙斯的成长,也是很有阐释的空间的。
希腊神话中的神就这样像人世间的人伦关系一样,有主有次,有父有子,有夫有妇,有兄有弟,但没有儒家式“孝道”和“三纲五常”,没有天尊地卑,没有父慈子孝,没有夫唱妇随等等。宙斯长大后也像其父克洛诺斯一样,不仅不“孝”,而且成为父亲的“死敌”。他逼迫克洛诺斯把吞到肚子里的孩子全都吐出来,这些“被吐出来”的孩子,也即宙斯的兄弟姐妹,就构成了奥林波斯山上的“诸神”。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提坦神族和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神族,如果按照儒家“辈分”而言,是“父子”两代神族,但正是这两代神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最终,奥林波斯神族取得了胜利。宙斯成为众神之王,也即第三代天王,希腊神话流传最广的动人故事正是从这里才开始。
我们在这里似乎有必要对宙斯前的原初神话和宙斯后的奥林波斯神话做出区分,才能理解古希腊人为什么能用这些神话传说来进行伦理教化,这些看似如同人类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父子相残、兄弟相煎、骨肉相害的神话,如何能够敦风化俗,培育美德,以举而措之天地之道义?我们似乎可以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诸神为界,把之前的古希腊神话作为原初神族的“自然状态”,而把宙斯之后的奥林波斯神族视为诸神的“社会状态”,因而神话描述神族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变“规则”的密码,才是我们理解所有西方人所领悟到的天地道义的原始秘密。
所以,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宙斯究竟靠什么取得了天宇的统治地位,成为诸神之王,他又将靠什么来避免之前的父祖神王被儿子阉割打垮而被取代的悲惨命运,以获得神之为神的尊严呢?
最初宙斯依靠“兄弟们”一起“子造父反”取得成功,这几乎是自然规律,每个最为威武、最有权势的父亲,最终总是要被儿子所替代,这属于通过神话最初反映出来的宇宙新陈代谢的规律。但当宙斯与其支持者打败了提坦神族,站立在奥林波斯山的权力之巅,与他的兄弟们面临如何分配世界的统治权时,这才反映出了对于人类而言的伦理难题。神族没有伦理困境,但此时如何分配统治宇宙的权力,神族也像人类一样,感到了问题的棘手,这也是神族首次遇到的“伦理”难题。
也正是在这里,西方伦理智慧的最早表现,即普罗米修斯的智慧表现了出来。理解神话中的伦理智慧,乃至天地神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普罗米修斯的智慧。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关系,如果按照我们儒家的辈分伦理,属于“堂兄弟”,因为他是提坦神族,但在奥林波斯神族与提坦神族大战之时,普罗米修斯非常智慧地选择了“中立”立场,实际上是站在了宙斯一边,这才使得他在宙斯取得胜利之后,能留在奥林波斯山,与统治世界的新神族兄弟们在一起。他的“智慧”在神话传说中最受赞美,他与人类的关系甚至比宙斯还更亲密与“仁爱”,因为他才是人类的真正“制造者”,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了人类,雅典娜赋予了人类以灵魂和神圣的生命,同时也是他为了人类能在茫茫宇宙中生存下来而不顾宙斯的禁令“盗火”给人类,同时赐给人类播种、建筑、纺织等实用技艺。这自然引起了宙斯的“勃然大怒”,于是宙斯用一条永挣不断的铁链将普罗米修斯缚在高加索的一个陡峭悬崖上,让他永远不能入睡,双膝再疲惫也弯曲不了,胸脯上还钉上一颗金刚石的钉子,一只可恶的鹫鹰每天要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尽管遭受如此不堪忍受的苦难,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坚决不向宙斯低头认错,硬是不屈不挠地忍受了下来,这简直就是后来基督教神学中耶稣形象的神话根源。这样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当初给宙斯的一个智慧,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他和神兄神弟之间对于世界的统治权,以避免骨肉相残的战争,后来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就是学习了这一点。这虽然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但以最简单的方式体现了宇宙的强调生而避免杀生的大德,因为在没有什么根据和理由决定谁是最高统治者时,如果没有这一“抽签”决定的程序,骨肉相残的残酷杀戮就会是人世间最为通常的做法,成王败寇使人世间成为最恶劣也最为愚蠢的丛林。
按照抽签的结果,三兄弟各管一方,宙斯主管天空,成为天神,以霹雳为武器,维持着天地间的秩序。大地不再由一神主宰,而是由三兄弟共有。而波塞冬(Poseidon)这位“二哥”主管海洋,成为海王神。他非常好战,但几乎是个失败者,经常以白马驾驶的黄金战车出场。只要他的战车在大海上奔驰,汹涌翻腾的波浪立刻恢复平静,并有海豚跟随;而一旦他愤怒起来,海中就会出现海怪。只要他挥动三叉戟,大海立刻就会巨浪滔天,风暴大作,海啸汹涌,甚至天崩地裂。而长兄哈得斯(Hades )成为冥王神,司掌阴间冥界,也被视为冥府中的“宙斯”。这样,“众神最后都凝聚成了一个大家庭——这一点也与人类相同,他们的首领和中心人物是人类之父、众神之王——宙斯,他真正的统治权仅限于天庭诸神,而海域和水域众神则听命于波塞冬,尘世和阴间众神则受哈得斯(普路托)的统治”(第5页)[9]。
因此,伦理的智慧,在宙斯的神界是以对统治权明确划分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宙斯成为主神,天庭诸神之王,取代了提坦神而成为希腊人崇拜的神,他的权力实际上也是与他的义务联系起来的,即维护天庭和世界的秩序,因为他“是自然界中一切生命之父,他的仁慈之手给大地带来丰收与富足。一切天空中的现象皆由他而起:他聚集和驱散云层,投下闪电,发出霹雳,给大地带来雨水、冰雹、雪花以及滋润的甘霖。他用他的神盾……呼风唤雨”(第15—16 页)。但关键的在于,宙斯成为天神之王后,宇宙不再是“丛林”,而是有“普遍法则”了:“宙斯在道德方面的含义对他们尤为重要,更令他们敬畏。因为他们把宙斯看作是不可更改的秩序与和谐法则的化身,这一准则是我们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道德界都要遵守的。与他专横、变化无常的父亲克罗诺斯不同的是,他根据严格的、不可辩驳的法则来驾驭和统治众神之国。”(第16页)
由此我们知道了宙斯这位天神的意义了。宇宙是个创生性的大自然,各种自然力以其自身的法则繁衍生息,生生不已,欣欣向荣,其自身必然的法则导致了自然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及其和谐共处的秩序,而宙斯代表的就是这种秩序与法则。就人类从属于大自然,是大自然的“造物”而言,人类生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这是最为首要的“伦理”。虽然人类有其特殊性,是自然界中唯一有理性、有自我意识,因而也知道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的存在者,但作为大自然的造物,必然像其他自然物一样服从自然界生老病死、荣枯兴衰的规律,因此,宙斯所代表的宇宙的和谐与法则,也就包含了,而非排斥了人类生活的伦常法则。神话对习俗的影响,首要就表现在神祇的生活对人类生活之秩序和法则的决定性影响。神既是人敬畏、崇拜的对象,也是人类模仿、学习的榜样。如果没有神话关于宙斯三兄弟以抓阄形式分权治理宇宙的传说,我们就很难想象,古希腊雅典城邦那么早地就开始实行抓阄式的直接民主制度。无论这种政治制度有多少弊端,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对以战争杀戮的形式定夺天下帝王统治权的古代丛林法则的一次决定性的文明跨越,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早成果,它既避免了以力杀戮的野蛮,也避免了在谁也没有完全正当性的条件下以“美德”为条件的虚伪做作。本来,如果没有宙斯,波塞冬和哈得斯都早就被父王吃到肚子里了,他们何德何能能与宙斯争权呢?但人的政治本性就是如此,尤其是在有天后赫拉(Hera,罗马神话中称之为“朱诺”)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一起“阴谋”的时候,一旦主观任性觉得兄弟们谁都可能成为帝王时,权力欲就是最为正当的生存意志。而神话的智慧,却给了兄弟们一个以轻松的抓阄来平分权力、各主一方的方案,这对于人类政治文明而言,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影响。
但宙斯这个众神之王也确实难当,因为诸神中的每一个都自由任性,却又有人类不可比拟的超人的力量和能力,这使得宙斯根本无法专制独断,但要“公正”地处理同其他主神(而且有十二个主神)的关系,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这些主神或者是宙斯爱戴的妻子,如赫拉;或者是兄弟,如海神波塞冬;其他各神也有沾亲带故的,有的是亲骨肉,如阿芙洛狄忒(罗马神话中称之为“维纳斯”)这个最美的女性身体象征和爱情女神,虽然按照《神谱》所传,是从天神乌拉诺斯被割而抛入海中的生殖器所化的泡沫中诞生,但按照《伊利亚特》记载,她却是宙斯与狄俄涅(Dione)的女儿。而战神和暴力之神阿瑞斯(Ares)也是宙斯和赫拉之子,是雅典娜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都是战神,但阿瑞斯作为战神,是肌肉力量乃至暴力的象征,他的战争代表了残酷与血腥。在《伊利亚特》中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好战之徒,唯一的兴趣就是驰骋沙场,他给希腊习俗影响最大的就是勇猛之德性,据说古希腊的德性areté就是来源于Ares,可见勇德之于古希腊的重要性。而雅典娜虽是女神,却同样是作为战神,常常让阿瑞斯成为她的手下败将,原因就在于雅典娜不仅勇猛同时还是智慧女神,说明战争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雅典娜同时还是艺术女神,她不仅传授给人类绘画、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且传授了纺织、烹饪、园艺、陶艺等工艺。尤其重要的还在于,雅典娜还是军事、农业、医疗、航海、驯马的保护神和法庭与秩序女神。传说雅典的第一法庭还是她创立的。
宙斯虽然是诸神之王,但他也不具有绝对的正义性和神圣性。他既没有东方诸神的端庄威严,也没有基督教耶稣的平易近人,更没有印度佛的大慈大悲。在他身上,人们看到的常常是咄咄逼人、专横跋扈的样子,一般男人好色风流、偷情通奸的恶习简直达到登峰造极。在为情所困时,为欲所驱地干坏事,也是家常便饭。如果按照道德主义的观念看待他,说他是“伤风败俗”“道德败坏”的典型,也绝不为过。那么,希腊人如何能用这样的神来敦风化俗?伦常教化的道德意义究竟在哪里?
说出来许多人会感到惊讶,在希腊古典文化中,更别说在远古神话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道德的概念,他们有德性概念,但“德性”是自然能力和品质的优秀与卓越,跟现代人的道德概念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神都是某一方面最为卓越的神力,但不是道德,要求一个神有人间的那些道德,就像要求一个古代中国皇帝成为只有一个妻子的好丈夫一样,是可笑而不现实的。
神话是先祖们自由想象力的产物,“半真半假”地传说神的来历、神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有的完全是一种心理学的“投射”,即把在有限的人类自己身上做不到,按照“人性”之“本能”原始欲望却想如此做的行为,投射到那些具有“神力”的神上,让他们替代人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神就是神奇,就是超越,就是做各种人类不可能做,做也做不好的事情的力量。所以,英国学者狄金森指出:“希腊宗教的特点,似乎是与良心无关。”[10]之所以与“良心”无关,因为神灵们要表达的就是各种神力按照内在必然性的任性张扬,这样才能满足人类想象力的美感,给人以精神的震撼和鼓舞,同时让人类看清自己的“天花板”,那不可超越的“必然”之神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崇拜敬仰,而不能妄言僭越的“绝对”。所以,神话张扬的是必然的真与美,而不是道德的善与良心。道德的善是因理性的自我约束而证成的“应该”与“当然”,神性的真与美是天性无拘无束的张扬所呈现出的自然而然的“自由”,是以其神力表达的“自然”之“自由”。因而,对神而言,他们没有“应该”,只有“必然”:
荷马作品中的诸神,从外表来看,其身体完全与人一样,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只是比人更高大、更美丽、更庄严,但人们也并未把他们夸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第2页)
神的力量当然也比人强大。宙斯只抖动一下他的卷发,整个奥林波斯山就会随之受到震动;其他各神也被赋予了强大的身体力量。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他们受到地域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无所不在,但这种限制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像凡人那样,因为他们能风驰电掣般穿越最远的距离。一眨眼的功夫,雅典娜就从奥林波斯山的山顶到了山下的伊萨卡,海域统治者波塞冬三四步就从萨摩斯达到了爱琴海中的埃维亚岛。(第2—3页)
那么,希腊神话对伦理教化的影响,首先是美的观念。正如我在本通史的导论卷《道义实存论伦理学》中所论:
希腊神话其实就是“美的宗教”,希腊人的理想,即美的理想,希腊文的善不是跟道德而是跟美通用的。……神话中的诸神区别于人类的,是他们生命的不朽,而这种不朽又恰恰不是指灵魂不朽,道德高尚,相反却是因生命本身的美,如体力、美貌、英勇和智慧而不朽。所以人们崇拜这些神灵,除了他们具有神力,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神的庇护(哪怕就是睡眠,也有“睡眠神”)外,是因为希腊神话是生命之美的宗教,诸神因生命力之美而不朽。这种美首先是身体的美,健壮有力、肌肉发达、比例匀称、魅力四射的体魄,这是神们尤其喜爱的。而心灵或灵魂的美善当然一样重要,它能赋予一个肌体以自立自主的生命气息,两者不和谐,就是坏的,是恶;两者都美,则和谐一致,在希腊人心中就“完美无缺”了。[11]
在此意义上,古希腊伦理文化的特点是不讲“道德”而讲“伦理”的文化。但这种“伦理”不是沉淀在人伦关系中的“亲亲伦理”,不是自我约束的禁欲主义伦理,而是以神采飞扬的美善张扬生命繁盛的德性伦理。在这种“德性伦理”中,强盛、强壮、生命力的张扬才是美之善,一切以神律作为“伦理原型”,或者说以“自然必然性”为“自由”之真理,追求正义的规范秩序的道义伦理。因为有对神律、宇宙大道的绝对敬畏和崇敬,才有那么大的自信力将祖先崇拜的各位神的“不道德”的“偷鸡摸狗”“伤风败俗”的偷情欢愉作为神性张扬的“任性”加以揶揄嘲笑,而非道德谴责。赫耳墨斯(Hermes)刚出生就能走出摇篮去“偷”阿波罗的牛;阿波罗一出生就有足够的力量舞弄专属于他的弓箭和竖琴;天后赫拉为了帮助处于急难中的希腊人,不惜“色诱”丈夫,对宙斯施魔法,让他把时间消耗在与她做爱后沉睡的过程中;女神阿芙洛狄忒与年轻力壮的美貌战神阿瑞斯“那种全属不法因而却也更加甜蜜的偷情窃爱行为”,被她丈夫抓住,召集所有的天神前来观看,它引起的也只是众神的“哄堂大笑”而不是道德谴责,凡此种种都凸显了神性生活的“超道德”,但有正义大道的伦理景观:
他们在道德上就高于人类,他们憎恶一切邪恶、不纯洁以及不公正,因而他们也惩罚人类的罪恶和不公正的行为;尽管如此,他们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恶习,如:欺骗与谎言、仇恨、猜忌、残暴与嫉妒等,也会干蠢事。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神圣,更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算是宙斯本人……也要永远屈从于决定他命运的旨意,绝无可能去欺骗、逃脱命运的安排。(第4页)
所以,希腊神话给希腊伦理的决定性教化就是,伦理作为存在之正道,是天地神人共生共存的法则,不单是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匡扶共同生活之正义,因为现实生活总是因不公不义而陷入野蛮、残酷和生死之斗争,如果要想在文明的、和平的、友善的秩序下过上神仙般的美好生活,那就必须要有伦理,它通过礼法制度,将人类生活纳入规范秩序之下,获得文明的形式。正如布克哈特所说:“对现实中的国家和法律的历史描述最早出现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它展示了一个充满不义的世界,诗人用个人的口吻呼唤信仰。与此同时,在没有祭司的时代,他成为他的同胞中第一个也是最令人尊敬的教师,如果能够悉心倾听他的想法的话,一定能够从中获益。”[12]
神话诗人于是成了最早的伦理教化的老师,古希腊人对命运的意识,对天命的敬畏就是通过神话而与对必然性普遍法则的敬畏一同建立起来的。神话赋予人类的一种伦理的希望就是,能像神那样卓越,因而依靠神性的卓越,做非自己不能做,非自己做不好的那种出于自身本质的卓越(德性)才能完成的事情,因而也能过上像神那样无所事事的、舒适的极乐(幸福)生活。这几乎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框架:伦理学作为属人之善,以美好生活,即活得好为目标,活得好的最高境界,就是思辨生活,思辨生活才最像神般的休闲舒适,对外物一无所求,成就自身的卓越。而古希腊伦理学除了在伦理上以正义为伦理原则来寻求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性规范秩序之外,特别看重的就是每一个存在者“是其所是”的卓越,这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真正路径。伦理追求正义,个人德性追求卓越,这成为古希腊德性论伦理学区别于所有其他文明的独特形式,无疑是神话诗教的教化产物。
当然,神话诗人也存在“伤风败俗”的方面,这也是需要在文明进程中慢慢加以清理的,最早在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十卷中,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柏拉图对神话诗教观念的无情清算。而在进入这一清算之前,我们必须考察古希腊实际的文明进程对塑造古希腊伦理思想的影响,尤其对人之德性塑造的影响。
第二节 文明进程
希腊早期的历史就是人神共居的神话历史,所谓“荷马时代”,即公元前11—前9世纪,属于古希腊的神话时代。一直到公元前8 世纪,赫西俄德依然这样说:“我将简要而又动听地为你再说一个故事,请你记在心上:诸神和人类有同一个起源。”[13]所以,从神话时代到古希腊,属于“史前史”,属于人神共居之传说的历史。到公元前8—前6 世纪,才被称之为早期希腊的“古风时代”,真正进入到希腊人的“历史”,它与城邦文化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之后才进入到哲学、文化的鼎盛时代,这是公元前5—前4 世纪前期,被称之为“古典时代”。最后到公元前4 世纪末—前2 世纪中期,希腊处于北方蛮族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奴隶制城邦衰落,最后为罗马所灭。
因此,我们要在这一希腊人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希腊历史的文明化,也即考察希腊人“伦理生活”在历史中的发生机制。这就是要考察它是如何将神话诗教中形成的道义伦理原则内化为城邦礼法制度,从而成为希腊人在伦理文明的发生进程中追求和成为有德性的人的“成人”机制。
在希腊历史中,这一点很清楚:文化基因的改造和传承,是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文明危机中发生的,不存在纯粹的“原始希腊人”或“土著希腊人”,因而也不存在作为纯粹西方文化基因的古希腊文化基因。“希腊”是在不同“族人”不断征服和被征服中,不断与“东方”(如腓尼基人、波斯人等)、“北方”(马其顿)、“南方”(如埃及)诸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形成、传承和创新的。
古希腊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多利亚人征服,发生在公元前12 世纪,这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两代,希腊人“英雄时代”结束后的“黑暗时期”,古老的文明因希腊人殖民扩散到整个爱琴海地区而消耗殆尽。此时拥有了铁兵器的多利亚人入侵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到之处,物质文明被摧毁,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而这又从反面给文化融合创新提供了契机,希腊之后开始兴起城邦文明。[14]
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平原少岛屿多的地形特征,是古希腊城邦文明兴起的地理条件。早期古希腊比较可信的历史叙述,也是发生在“多利亚人入侵”之后,而这之后的希腊文明就是随着城邦的兴起而确立的。最早的城邦大约是在公元前10 世纪由入侵者多利亚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科尼亚(Lakonia )建立的斯巴达城,史称拉凯达伊蒙。它由四个村庄组成,人口显然不多,面积也不大,但斯巴达城邦后来一直像雅典城邦一样属于古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它们构成了古希腊最为著名的城邦典范。
雅典人宣称他们是希腊的土著民族,但雅典人显然不是多利亚种族,在多利亚人入侵之前,雅典至少有两个很古老的所谓土著:“土著的阿提卡人”和“移民伊奥尼亚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3卷第685、689行)中,雅典人被归结为‘伊奥尼亚人’”,但伊奥尼亚人本身就是移民到阿提卡的,“我们也许有比较合适的理由把这些移民称之为伊奥尼亚人”。[15]因此,雅典城邦文明本身是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不存在单一的“土著雅典”文化基因。如果说有文化基因的话,它也不与特殊的土著族群相关,而是与神话相关。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开篇就说:
雅典人起初曾有一个王者政府。当伊嗡[即伊奥尼亚人的祖先]和他们一起居住时,他们才第一次被称为爱奥尼亚人。……雅典人尊敬祖先阿波罗,因为他们的军事执政官伊嗡是阿波罗和克绪托斯之女克勒乌莎的儿子。[16]
作为城邦文明的典范,雅典文明经历了如下几个关键步伐。
(1)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晚期,提修斯(Theseus)完成了阿提卡城邦的统一,提修斯还不被视为城邦范围内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神灵受到部分居民的崇拜。但提修斯是真值得崇拜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提修斯是倾向于庶民的第一人,而且放弃了君主制政府”[17]。
(2)梭伦(Solon)立法与民主制的奠基。城邦是人为好生活而建立,而不是相反,人为了城邦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这一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希腊人能够在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领域独领风骚之后,在东地中海世界很好地发展起来,完全依赖的是伟大的城邦文明:“随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邦文化——古希腊文化的成熟,东地中海有了很好的发展。……但希腊人仍然保持了免于外国统治的自由,并且在他们的城邦中建立了自由人的社会,因着这些人的努力,古老的城邦达到顶峰。”[18]雅典城邦就是建立在独立、自治和城邦自由人的伦理基础上,其主体单位是自由民,而不是血缘家庭,但一开始“胞族”在城邦分区管理中,是有一定分量的。他们开始是按照“自然”分区管理:一年有四季,他们便把城邦分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分三个区,因而像每年有十二个月一样,雅典有十二个区。每个区都有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每个氏族包含三十人,可见人口不多。但到“公元前7 世纪初,雅典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掌握在三位一年一选一任的官员手里……执政官是审理民事案件的最高法官。就职时,他会庄严宣布在其任期内确保每一位公民的财产完整”[19]。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的发行,与周边城邦贸易额的扩大,特别是雅典发生了与麦加拉(Mégara)的战争,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恶劣,自由雇工的境况也凄惨,富者越富对贫者的剥削和压迫越重,社会矛盾因而愈演愈烈。这时一位商人出身的贵族贤人梭伦(希腊“七贤”之一)不负众望,在公元前594年(泰勒斯[Thales]开始作为哲学家出现的时候)出来作为调停人,被任命为执政官,大胆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化解了城邦政治危机。他的改革,亚里士多德做了这样的评论:
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民主特色的大概有以下三点: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官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20]
梭伦改革不仅在城邦文明史上,更在人类伦理史上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重大事件,他的第一个社会改革措施,确实是减负令(Seisakhtheia),这是所有改革者后来都知道做的事,但他通过立法所实现的减负,即取消所有以人身为抵押的债务,这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人类文明的高度,它首先防止了人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的危险,因而让即便是欠债的穷人,也保持“人身自由”,而不被当作非人格性工具——奴隶——来被奴役的可能性,这真不仅对当时成千上万的可怜人是福音和希望,而且是人有尊严的、有德性的、有品位的起点,保有这一起点的文化才有文明的品质。所以梭伦改革对伦理的伟大贡献就是自由和公道的美德,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他:
梭伦在一些方面扩展个人自由,但在另一方面又限制人们的自由。通过防奢法和防惰法,他力图限制个人自由,违反者将受严惩;通过允许无子嗣的个人订立遗嘱,将财产遗赠给他指定的而非最近的亲属,他扩大了个人自由。……
梭伦改革虽然很有胆识,但他颁布的一切措施皆完全依法行事。他并未让自己成为僭主,虽然他本可轻易为之,而且许多人也希望他这样做。相反,梭伦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预防可能出现的僭主制度。……梭伦表明了他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每个等级公民享有的权力应当与其承担的社会义务成正比。这是他立法活动保守的一面。……卸任时,他备受人们的抱怨和攻击,为此写下一些哀歌体诗歌为自己辩解。他说他秉承的是中庸精神,坦承其所作所为公正无私。
梭伦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在他身上,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早期希腊人的高尚道德情操,也体现出希腊贤者的伟大。[21]
这种改革奠定了希腊民主制的法治基础,民主伦理的基本原则确立了起来:公民自由,权利与义务对等,遵纪守法,公平正义。这为促进雅典在公元前6 世纪的强势崛起,做好了充分准备。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合力的结果,不是伦理之善的单线演进,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缘于人性人心本身的复杂性,民主政治本身的党争带来的各种利益和权力的纠葛,也让以伦理提升文明的难度变得格外艰难,它如果没有严格阻止向其自身的反面堕落的“熔断机制”,民主制转化为“僭主制”也就一念之差,一步之遥。梭伦改革成功退位之后,在他的晚年,他就非常悲哀地看到,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利用改革后经济繁荣和政局稳定进一步解决了梭伦未解决的贵族间的斗争而博得了荣誉,但同时也把自己成功地变成了梭伦坚决不愿为之的“僭主”。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27年死后,长子希庇阿(Hippias)继位,就让希腊民主制一时成为泡影,更糟糕的是,雅典随后走向了扩张的帝国之路。谋杀、兄弟相残、弑君这些与文明背道而驰的行为总是与“僭主制”如影随形,必然会葬送城邦美好的前程。因此,在雅典未能取得民主制度真正胜利之前,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巴达城邦一跃而起,成为主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在公元前6 世纪下半叶也就成为希腊大陆最强大的城邦。
城邦文明于是具有了两个不同的样板。“僭主制”因缺乏伦理道义总不可能引导城邦走入繁荣与发展,僭主自身的垮台和暴死一直是必然的事情,需要的只是时机。在斯巴达的帮助下,雅典成功地推翻了僭主的统治,重获自由,但代价是,必须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唯斯巴达马首是瞻”。但此时东方古老的波斯帝国开始了对希腊的入侵和征服。这之后的历史一般人都比较熟悉,是通过两场大战来展开的,即希波战争[22]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对这两场战争的历史分析,不是我们的任务,而这两场战争所反映出来的伦理与文明的关系却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3)希腊人的同盟意识和战争伦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作为希腊殖民地本来是不团结的,长期分裂与不和,使得他们沦为一直任人宰割的猎物。但通过希波战争,他们摆脱了波斯的侵略和征服,反而激化了希腊人的同盟意识,他们才有了“希腊人”的意识。这种对“希腊人”的共同意识,是由一个绝对他者,“敌人”,要来入侵和奴役“我们”的“敌人”激发出来的“同族认同”。但如果仅仅是有“认同”的意愿和意识,没有共同的“组织原则”和“行动原则”,对于一个军事性的“同盟”依然是不现实的。希腊人同盟意识的觉醒,之所以对希腊伦理具有重大影响,就在于他们开始探索大小不同、贫富有别、文野悬殊的诸多城邦,如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能够组成一个“希腊同盟”,“勠力同心”在和平时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自打着小算盘时是很难做到的,但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时,不采取共同行动,不遵循共同原则,大家都得被征服和奴役,于是便能形成“共识”,这也是“战争”唯一能在“伦理”上获得辩护的东西。确实“希腊人”的共同意识是不得不结成一个“希腊同盟”反抗波斯侵略而形成的,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才使全体希腊人摆脱被侵略、被征服的地位,从而走上自治、独立和自由的繁荣之路,这是民族伦理共同体在实践中必须考虑的大事。
(4)雅典城邦文明的典范是依赖于实践智慧完善了雅典民主制,这得感谢一位城邦立法者,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最有实践智慧的人物,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前429)。成就伯里克利智慧的,有三位“老师”,一是他的出身名门的母亲的教育,他母亲是梭伦改革后让希腊民主制真正取得了胜利的立法者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侄女,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使得伯里克利时刻保持着高贵气质,连平时参加非常习俗的酒宴他都力求避免;另两位老师,一位是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雅典人达蒙(Damon),另一位是我们在哲学史上熟悉的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阿那克萨哥拉是雅典的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真正对政治家起到指导作用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上与原子论者非常相同,他提出“种子说”的世界本原论,按照多元物质元素的“聚合”与“分离”的原理,解释事物的形成、发生和发展,尽管19 世纪的德国著名哲学史家策勒(Eduard Zeller,1814—1908)批评他“不承认绝对的生成和毁灭,不承认原始物质的性质变化……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都采取了这样的权宜之计:把生成还原为实在的结合,把毁灭还原为实在的分离”[23]。这种“权宜之计”也许在阐释世界本原的“科学性”上具有不彻底的“猜想性”,但对于城邦人共同存在的“伦理机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实践智慧”。城邦各个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等级、不同诉求的“公民”,如何在一个公共性的城邦中能够活出人的品质,稳定而不变的精神品质,这是城邦好生活的一个标准,也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成就的标准,因而需要阿那克萨哥拉“种子”说的“聚合”与“分离”的原理。在这个原理之外,阿那克萨哥拉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灵魂中的最高认识能力“努斯”概念,这样的自然哲学显然为伯里克利的民主制改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理论支持。
伯里克利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完善,一是引入了一系列制度,让参与城邦政治的每个人都获得恰如其分的权利和义务。譬如,执政官和五百人议事会成员都可领取一份薪酬成了一项制度,这解决了贫困者也能参政的难题,尤其是激活了代表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民众法庭这个民主政体的精华体制;同时富裕的公民必须承担公共负担,这些制度化措施既维护了城邦的聚合性(团结和稳定),又保持者每个人积极参政议政、出谋划策、群策群力的活力,也让伯里克利真正地赢得了民心和声望。另一为伯里克利赢得声望的事是通过大规模重建神庙而让他功勋卓著:
在这方面,伯里克利展示出他的伟大和过人之处。他能觉察到大规模修建神庙的重要性,认为一个赋予神灵高贵圣殿的城邦一定会使她本身成为一个崇高城邦,通过修建华美的神殿,城邦以一种更有价值的方式展现了她的实力和理想。[24]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真正崇高的民族宗教对于人们精神生活,从而对于伦理的最为积极的影响。通过华美的神殿的建造,也带来了希腊艺术的繁荣昌盛,菲迪亚斯(Phidias)成为伯里克利时代造型艺术的代名词,将古希腊造型艺术之美塑造成为古代美的典范: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将这种古典美的典范概括为“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称为现代新古典主义艺术理想的灵魂,这种艺术美的理想也是塑造古希腊伦理的一项十分关键的精神要素。
第三节 “归家”本义
“伦理”(ethos)的概念来自“习惯”“习俗”,这为人所周知,但如果人们只是将“伦理”等同于“习俗”,那也会让人感觉到其俗不可耐的无知与肤浅。“伦理”的本义是“家”“居所”“住处”,在其中庇护人性的东西之成长与到达(Ankunft),同时也只有“家”才是自己可以“任性”也有人在意你任性不任性的地方,因而在每个人的心中,无不根深蒂固地存在对“家”的思念、对“归家”的渴慕,当然这种情感本身也对应着“无家可归”的惆怅和“有家难回”的乡愁,这都是伦理“原义”所包含的意蕴。古代伦理学的魅力其实就是关于“筑家”与“安宅”的智慧。随着现代道德哲学越来越精致化和分析技术化,关于家的原义总被遗忘,因为伦理学从家中的德性涵养转向了对外部行为正当性的规范性奠基,当我们偶尔在黑格尔[25]和海德格尔[26]那里见到伦理原义的考证,总是感激其学识的深厚。而对“伦理”这一原义及其困境的展示,正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题。
荷马两部史诗是有连续性的“历史”故事。《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人为了争夺美貌绝伦的海伦(Helen)而不惜进行了气吞山河的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这也充分反映了希腊人为美而生、为美而死的习俗。战争的起因是特洛伊(Troy)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s)的英俊王子帕里斯(Paris)受阿芙洛狄忒的唆使,到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家做客,宴会上引诱并迷惑已成王后并养有一女儿的海伦,之后趁墨涅拉奥斯去克里特岛(Crete)招呼她在家好好待客之机,令海伦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跟着这个不被看好的王子来到了特洛伊,从而招致墨涅拉奥斯王的极大愤怒,说服希腊其他各邦组织了强大无比、包含各路英雄豪杰的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甚至奥林波斯山的诸神都因各种关系明里暗里参与了战争,因而最为充分地展示了各种神性和人性的智慧以及各路英雄豪杰的德性与劣性。本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伊利亚特》写到赫克托尔的死就结束了,因为希腊人最终将特洛伊城洗劫一空,烧成灰烬,男人大多被杀死,妇女和儿童大多被卖为奴隶,金银财宝装进了希腊人的战舰,海伦也被墨涅拉奥斯王带回希腊。但《奥德赛》接着描述英雄们的返家之旅,他们不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凯旋,反倒是逃离战场和搏击海浪的浪迹天涯之艰难与挣扎。主角奥德修斯(Odysseus)在其他将领和壮士尽数还乡之后,却因惊涛骇浪翻船落海,海上女神卡吕普索(Calypuso)救起并爱上了他。卡吕普索在众多女神中虽然并非特别耀眼,但她出身名门,是托起天穹的大力神阿特拉斯(Titan Atlas)的女儿,据说是“最完美的情人”,但毕竟大海只属于少数英雄的落难之地,而并非普遍凡人的舞台。哪怕是大海之女神,“完美的情人”,也只能迎着风浪,守着孤独。因此在她救起奥德修斯之后,就爱上了大英雄,不仅承诺给这位世间的王者过上天堂般的幸福,而且许诺其永生不死,于是,《奥德赛》开头有如此描写:
此君一人,怀着思妻的念头,回家的愿望,
被卡吕普索拘留在深矿的岩洞,雍雅的女仙
女神中的佼杰,意欲把他招作夫郎。[27]
对于一般的凡人,遇此女神的欢爱,能享受天堂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极乐之福,是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但古希腊人在史前时期可能就深刻领悟出了人有人的天命,人之为人根本就享受不起神仙之快乐,人类有其自身的劳作之命,只在艰辛的劳作中,因自身之德性而“活”出来的幸福,才是属人之福,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神样的”奥德修斯在经历了女神长达七年的爱与永生之福的温情脉脉的善意挽留,依然毫无动心,日夜思念家中的凡妻,渴望早日回归凡人之家这一选择的真意:
当他们享受过吃喝的愉悦,
丰美的女神卡吕普索首先开口,说道:
“莱尔忒斯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啊,
还在一心想着回家,返回你的
故乡?好吧,即便如此,我祝你一路顺风。
不过,你要是知道,在你心中,当你
踏上故土之前,你将注定遇到多少磨难,
你就会呆在这里,和我一起,享受
不死的福分,尽管你渴望见到妻子,
天天为此思念。但是,我想,
我可以放心地声称,我不会比她逊色,
无论身段,还是体态——凡女岂是
神的对手,赛比容貌,以体型争攀?”
听罢这番话,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答道:
“女神,夫人,不要为此动怒。我心里一清二楚,
你的话半点不错,谨慎的佩涅洛珀(Penelope)
当然不能和你攀比,论容貌,论身型——
她是个凡人,而你是永生不灭、长生不死的神仙。
但即便如此,我所想要的,我所天天祈盼的
是返回家居,眼见还乡的时光。倘若
某位神明打算把我砸碎,在酒蓝色的大海,
我将凭借心灵的顽实,忍受他的打击。
我已遭受许多磨难,经历许多艰险,顶着大海的
风浪,面对战场上的杀砍。让这次旅程为我再添一分愁灾。”
他如此一番说道。其时,太阳西沉,黑夜将大地蒙罩
他俩退往深旷的岩洞深处,
贴身睡躺,享受同床的愉悦。[28]
什么挽留也没用,什么艰难险阻也不怕,外面的世界哪怕再好,却总是执意要返回“家居”,与凡人妻儿一起过有艰辛劳作的生活,凭自身的德性“活出”美好人生之福,这就是“伦理”的力量所在。归家与还乡成为“伦理”寓意最深的隐喻。
因此,以为只有儒家才从“家”出发探究“伦常”关系,这是一种误解。古希腊人同样关心“家”或“居家”,但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以及“家”的伦理意蕴的理解确实不一样。他们更加强调男女因美善而自由生发的“爱情”,而不是把自然的“亲亲”之情作为伦常。伦理的东西源自自然,但不直接等同于自然,而是必须高于自然,作为对自然东西的庇护、涵养与完成,因而作为“第二自然”,这样的“伦理”才是规范的引导与教养的体现。奥德修斯拒绝美貌超群的女神之爱,念念不忘平凡的夫妻之爱,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爱情的一种理性主义理解。爱是一种平等关系的相互承认的情感,平等的人与人之间都有爱的禀赋,但神与人之间的差距太大,大到超出了友爱的范围,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才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也列举了卡吕普索的例子。不仅奥德修斯这样的英雄,就是出身名门的他的妻子佩涅洛珀也是坚贞不屈地信守爱情的。在经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又经历长达十年充满艰难险阻的归家之旅,居家的妻子除了日夜思念丈夫的归来,之外,她在家乡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惑呢?
荷马给人们呈现的是一幅希腊古时社会习俗的画卷:108 位佩涅洛珀的求婚者蜂拥而至,全都是豪门贵族,“其中56 个来自奥德修斯统治下的伊塔卡和其他海岛,52 个来自附近的岛国。佩涅洛珀被迫要从这些人中选出奥德修斯的继任者。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这都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求爱”[29]。这是私家与国家的政治学,在私家,她既要面临公公这位老国王的压力,作为妇女,她无权管理这个城邦,也要面临成人了的儿子的压力,儿子始终也并不清楚母亲是否能够抵抗这些外部压力,坚守到父亲归家;更直接的是面对这么多求爱者每天居家吵闹,甚至公开威胁,如果不答应求婚者,他们天天在这里吃光她的家产和财富。而她必须想尽各种办法予以拖延。如果一两天、几个月的拖延,办法总能想出,但奥德修斯生死不明、长达十年海上漂泊,一个母亲没有对爱情的执着,没有对家的坚定不移的坚守,是无论如何也拖延不下去的。我们只能在黑格尔的这一表达中体会一个女性坚守爱与家的艰辛:
人们总以为,哲学所带来的,就像佩涅洛珀的织物一样,是一种过夜即废的东西,每一天都从头开始。[30]
佩涅洛珀靠无目的地纺织她的织物打发无尽的黑夜和可怕的孤独,她白天忙乎在偌大的织机前,夜晚则点起火把,将织物拆散,以便从头纺织。一连三年,每天要处理的问题是同样的,守住爱与家,打发求爱者的纠缠,而每一天面临的处境和形式又都是全新的。这确实需要哲学的智慧,也如同哲学的修行。哲学总是思考那永恒的问题,却总是在思考者所面临的当下处境中寻找解决的答案。任何一个有经验和知识的人,都会体会到佩涅洛珀执着于不变爱情的艰苦和内心的无比强大。
奥德修斯同样的艰难,这位在政治和军事上足智多谋的将领,我们只需看看《伊利亚特》对他的描述就可知道他简直是个集男人之美德于一身的卓越人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参加了希腊使团去见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因帕里斯劫夺海伦而引起的争端,可惜这一和平之旅没有取得成功。在希腊联军连续九年的进攻而不克之后,在第十年是因他献计的“木马”最终才里应外合攻破特洛伊,这是特洛伊战争中最为经典的一个计谋。因此,我们只需阅读《伊利亚特》第十卷(标题是“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夜探军营”)就可以发现,用在他头上都是如下这些美德的修饰词:
“闻名的枪手”(110),“聪明如宙斯的”(138),“宙斯的后裔”(144,339),“宙斯宠爱的”(527),“足智多谋”(144,148,382,400,423, 554),“可敬的老人家,你真是个倔强之人”(167),“坚忍不拔”(230),“神样的”(243,460,488),“坚毅的神样的”(248,498),“做完祷告在茫茫黑夜中继续前进,像两匹狮子,越过杀人场、死尸、甲仗和黑色的血污”(296—298),“光辉的”(544),“阿开奥斯人的荣耀”(544)[31]
可见,用得最多的就是“神样的”“足智多谋的”,即便如此,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他与普通人一样,面临太多的困难与艰辛。他的艰辛除了难以摆脱女神的爱情绳索之外,主要的是先得罪了归家必经之路上的海神波塞冬,因为他刺瞎了波塞冬的儿子,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奥德修斯并非不敬神之人,我们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他每次做重大事情之前都虔诚地向宙斯或雅典娜诸神祷告,请求神佑。但人的命运免不了有时不得不得罪某些神,而对波塞冬他不仅是得罪,更是引起了波塞冬极大的愤怒。原因是他和他的随从漂泊在海岛上,遭到了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的囚禁。这位海王之子,不仅相貌奇丑无比,粗壮的四肢长满了海藻般的汗毛,布满皱纹的额头下长着一只非常巨大的独眼,还有一个又大又塌的鼻子,而且性格极为残暴。奥德修斯思乡情急,他的船队离开特洛伊后,先是遭到喀孔涅斯人的袭击,漂流到另一个海岸,一些船员因吃了“忘忧果”流连忘返,不想回家,好不容易到了这个海岛,却被这么一个家伙囚在一个山洞里,而且他每天都试图把手伸进山洞,抓一头羊或者船员吃掉。奥德修斯为了自救,将找来的木棍在山洞的岩石上磨成了尖状,等波吕斐摩斯把手伸进洞口,将眼睛凑过来向洞里看的时机,刺瞎了巨人的独眼,把活着的同伴一个个缚在羊的肚子下面,逃出了山洞。所以,波塞冬得知儿子被刺瞎后发誓报复,在奥德修斯回家的海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他归家的决心。他之后战胜了魔女基尔克,抵挡了海妖塞壬美妙歌声的诱惑,最后于第十年侥幸一人回到故土伊塔卡,装扮成乞丐,进入王宫,设法同儿子一起杀死那一伙占据着他的王宫,挥霍他的家财,疯狂追求他妻子的求婚人,最终与爱妻重新团聚。
所以,奥德修斯的“返乡之旅”,被黑格尔称之为“人类精神的奥德赛”,历来就是哲学或伦理寻求“返回家园”的隐喻。
与过分重视家庭私德的儒家家庭伦理不同,荷马其实并没有过分强调奥德修斯的私人品质,哪怕赞扬得很多的世人一般看重的英雄的第一美德“勇敢”,荷马也总是与“足智多谋”的理性智慧联系在一起。所以,勇敢、智慧等美德总是与城邦正义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杀死那么多的求婚者,《荷马史诗》也暗含着批评,虽然在古代,“复仇”是恢复“正义”的最直接方式,
《荷马史诗》之后的传说对奥德修斯的经历有许多补充,把他的私德上的缺陷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把他描绘成一个虚伪、狡诈、胆小的人,但总体上,他的许多行为恰恰是作为人而对诸神时常不关心和支持正义的不满,而自主甚至任性地果敢行正义之事的表现:
奥德修斯了解,诸神并非总是能够捍卫正义的事业,有时甚至没有这样的意愿,这种了解似乎导致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后果,使奥德修斯只能教会自己,要更加独立于诸神。这似乎也使得他弱化了对正义的依属,强化了他无所顾忌地行动的趋势。[32]
但《荷马史诗》对其主角的归家的伦理隐喻,也没有让古希腊伦理将重心放在血亲“私家”的伦理建构上,而是始终关注城邦之“公家”的公正伦理,以对城邦公正的关心和维系,涵养每一个人伦理德性之品质。
这反映出古希腊人与我们儒家之“家”具有不同的伦理构成。除了夫妇、父子关系相同之外,古希腊人是把“兄弟关系”放在城邦公民伦理中处理的,而作为家庭成员的,实际上还包括完全不具有血缘关系,更非同类人,甚至在政治习俗上不具有“人格权”的“奴隶”。因此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也是古希腊家庭伦理最为重要的一伦。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关系,就是“帮工”,他不像奴隶,不算是“家庭成员”,但古希腊的制度习俗,贵族之家的生产劳动,除了家奴就是“帮工”来做,这样一来,古希腊的“家”更是一个社会单位,血亲关系反而是其次的:
凭借权力专制的家(oikos)这一核心,人们得以组织自己的生活。Oikos的好处不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包括安全保护),也提供伦理规范、价值观念、职责、义务和责任、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Oikos不仅指家庭,也指整个家庭的成员、田产和资财的总和。因此,“经济”(economic,来自oikos 的拉丁化形式oecus,即对oikos的管理之术)一词就意味管理家产,而非维护家庭和谐。……
就负面而言,成为他人之oikos的一员意味着丧失大量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然而这些人既非奴隶,也非农奴或契约奴。他们是家臣(therapothes),用服务来换取在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中的位置。[33]
所以在伊塔卡,家臣或帮工(thetes)并非oikos成员,其地位比奴隶更不如。总之,古希腊的“家”(oikos )更像是以地产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组织,一个消费单位,而不单纯是血缘家庭。它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其源头,以宙斯为天王和人类之父而组成的“天庭”,就是包含天地神人乃至各种“造物”一起组成的“宇宙之家”,宙斯等诸神,也结婚生子,但他们活动的舞台,从来不以“私家”为单位,“在伊奥尼亚的各个城邦里,宙斯要所有的公民成为真正的兄弟。公民在各自的氏族内部就像在同一个大家庭中生活一样”。宙斯他的政治权力是家庭的权力,与儒家家长“家庭的权力”是“政治的权力”,具有完全不同的伦理维度:
在与赫斯提[即希腊神话中的灶神或家室女神]有限的联姻中,宙斯既控制了每个住所中的个人家园——在这个特定的中心构成了家庭扎根其中的种脐——也控制着住在城市中心通行的、执政法官监督的赫斯提共同语言(Koine)的城邦大家庭。家长宙斯是隐修的宙斯,他圈定了家长理所应当行使权力的范围。[34]
所以,希腊“伦理”之“归家”的隐喻,不单是回归“亲亲”的小家,而是具有“家神”主宰、充满友爱精神却又需要公平的大家。“伦理”之本义,作为“家务”建构oikos 的共同生活机制,它既是共处的公共精神纽带,也是相互交往的规范礼节,更包含亚里士多德后来所讲的“家务”(ὀικονουνια)即“政务”和“致富技术”,它不仅要处理“配偶关系”和亲嗣关系[35],而且要处理主奴关系,家庭成员与帮工的关系,因此,“爱”(包含“情爱”“友爱”和“仁爱”)、“正义”和“自由”才是这种oikos 伦理的主题。
第四节 德性文脉
希腊神话传说的是诸神和英雄的德性,这种“德性”之“善”不是现代个人行动的“道德性”(morality)之善,而是“率性之谓道”意义上的自由与性情的真与美。“既美且善”(καλός κἀι ἀγαθός)、以美为善的观念[36]是希腊神话奠定的德性文脉之基,它不仅使得希腊伦理而且使得整个西方伦理都未走入严格他律的“道德主义”,这全然得感激古希腊人所敬畏的大神身上无不具有的率性为道的自由与美善。
伦理学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与身心愉悦、激情快乐、个性生命力的张扬联系在一起,而不与悲苦、禁欲、压抑、束缚和专制联系在一起。自由、美善、正义、爱情、友谊、个性张扬、激情澎湃、生命力丰饶等所有构成美好生活的元素,神话都给出了“原型”,从而也赋予了希腊伦理总体上一种积极向上的对待人生悲剧的乐观主义色彩。人类都得忍受必有一死的生命短暂性命运,服从自然的生老病死的因果律,但人有德性在短暂生存中,活出人生的精彩与卓越,这是整个希腊德性文脉的主调。
神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向导与理想,其中的中介是“英雄”。神话中的英雄都由神所生,为神人所共爱,但我们由人所生的凡人同样也可以成为“英雄”。神话中的“英雄”,都有战争中的力量、英勇与睿智构成其德性的基本品质,而神话导致的英雄崇拜,在希腊城邦文化中得以延续,靠的是从荷马时代起发展起来的“体育竞技”。这是在平凡的人类生活中,以自由、健美和“德性”(“优秀”意义上的)产生“英雄”的伦理机制,因为这是通过公平的“竞技”“竞赛”产生大众“偶像”的机制,它带给古希腊一个有别于神话英雄而属于伦理社会的“德性”概念:
竞赛(agon)扎根于荷马时代人们的竞争伦理中,那时它构成了其军事首领角色的基础。但在古风时代,它被转变为文化活动——一种为竞赛而进行的竞赛,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优异[即“德性”]与出身被等同起来,“贵族政治”一词的本来含义是“最优秀者的统治”,他们的优异(areté)要通过竞赛中的成功来证明。[37]
“竞赛”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需要通过公平的竞争来显示自身的优秀或卓越。所谓公平竞赛,就是有事先制定出的规则让大家遵守,它能让“参与者”不再仅仅通过“身份”“地位”而通过自己在遵守共同规则基础上的成功来证明自身的优秀,继而通过“优秀”获得相应的荣誉、成就和地位。因此,在古希腊文明中,它与贵族生活方式所要求于人的高贵品质相应地发展和完善起来,同时也是名门望族、政治精英的“名望”所凝聚起来的尊贵性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
自克利俄丰(Cleophon)以来,人民领袖不断地一线相承,尽是些最喜欢鲁莽行事的人,他们使多数人满意,目的在于获得当前的声望而已。继早期的一些政治家之后,在雅典认为最好的政治家是尼克阿斯,修昔的底斯和塞剌墨涅斯。对于尼克阿斯和修昔的底斯,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他们不仅是有荣誉的君子,而且是政治家和整个国家的爱国公仆。但是,对于塞剌墨涅斯,意见就有分歧了,因为恰巧在他那个时代,宪法发生了变动,性质十分混乱。[38]
这说明,人的高贵德性表现在做事不鲁莽;为人处事讲荣誉、体面,具有君子风度;是爱国公仆。至于是否真是爱国公仆,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有“宪法”依据的,也就是:
他总是引导一切政府走上完全守法的方向,因为他善于在一切政府之下为国效劳,这是一个善良的公民应有的义务,可是,当这些政府行为不法时,他就绝不附和它们,敢于对抗它们的敌意。[39]
所以,无论是贵族还是一般公民的美德,都需要在良善的城邦礼法范导下才能培养和塑造出来,不是闭门修身的结果。这是古希腊人不从血缘家庭的亲亲之情,而从城邦礼法来教化涵养人的美德之缘由。亲亲之情,是自然之情,凡人都有,无人不重视,但要把这种自然之情培植为美德,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必须向“道德情感”转化,这就需要情发自然而尊义守法,从而本着善意、礼义待人,让正义友爱之情统御人性诸德,这样的道德情感才是城邦美德之根基。城邦承担着教化公民的使命,但不依靠宣传和鼓动,而依赖良法善治。城邦礼法最具规范的有效性,如果政治家真心做“爱国公仆”,就会自己带头遵守自己制定而让全民遵守的礼法,引导政府走上守法正义之文明方向。倘若政府与国王都能守法,百姓公民就没有谁敢违法。城邦政治家的德行操守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典范性的榜样,因此,贵族爱荣誉和追求体面,也与这种影响力巨大相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过:
一个父亲询问,要在伦理上教育他的儿子,用什么方式最好,一个毕达哥拉斯派的人(其他人[指苏格拉底]也会把此挂在嘴上)做出的回答是:“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善法律之国家的公民。”[40]
这说明,至少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约前500)这个公元前6 世纪、第一个命名哲学为“爱智”的人(他当时还不属于希腊本土人)开始,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人的德性养成不在家庭私人关系内,而在城邦公共生活中成为“公民”,学会做一个好公民所必需的遵纪守法,从而理解并自觉履行自己在城邦中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后来希腊民主法治文明的伦理德性基础。
有人认为古希腊的德性本质上是贵族式的力、美、成功与荣誉的美德,此乃以偏概全,贵族式美德带有更多的古风,但并不能作为古希腊伦理文明的本质,因为民主法治才是真正让希腊文化文明起来的制度基础,贵族的美德除了遵从这些表浅可见的价值外,还有精神的自由与高贵,对公共责任的义务担当,这种精神品质以守法正义、平等公正、平和中道、无私奉献为荣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贵族制为何可以成为最好的政体就是从公共的善德立论的:
严格地说,只有一种政体可称为贵族(最好)政体(Aristokratien),即由最有德性并因此是最好的男子汉来当政,他们的好可不仅仅是出于相对的好,而是绝对公道正当地为贵族制赢得美名的最佳品质。只有在这种体制中,好人和好公民才是绝对同一。(《政治学》1293b3—5)[41]
也就是说,贵族制是让最有德性的人当政,这种体制能让“好人”与“好公民”同一起来,亚里士多德主要说了如下理由。
第一,这个政体是让最好的人取得最崇高的地位,因而它具有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让人趋向卓越,因而贵族制向善的倾向是其他政体不可及的。
第二,政府如果不是由最好的公民当政,而由贫穷的阶级做主,就不可能导致法治。法治无论对于城邦还是对于城邦中的每一个人,包括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都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形式,只有在良法中,人才能自由自主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成就自己的品质,实现人生的幸福,如果当权者带头乱法,城邦就会失去秩序,人民就会相互伤害和争斗,结果无人能够活得好:
一个具有贵族制的城邦,如果不是由最好的人统治,不能形成合法的公序良俗,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城邦由最恶劣的人统治。所以,一个法治的却尚未秩序井然的城邦,就应该由最好的贤德之人来统治才是贵族制的。但是,如果制定了良法,却得不到遵循,在这里也就不存在一种好的法治秩序。所以,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颁布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既可服从良法也可服从恶法。(《政治学》1294a1—6)[42]
在这里我们立刻会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广为人知的名言:在城邦中,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因此,德性不是天生的,不是靠出身名门能成就的,而是在好的城邦礼法中被教化而成的。这一思想,成为希腊人对于德性的基本认识。
第三,具有良善礼法的城邦,才能养成公民之间相互友爱的美德。如果相互仇恨代替了友爱,人们连走在同一条路上也不愿,就不可能结成共同的社会团体了,只有相互友爱,社会生活才是可能的。而相互友爱的社会,靠的是城邦良法善治,良法合情合理地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生活才具有规范,大家都能安心于各自平和稳定的生活,既不觊觎富人的财富,也不对别人抱有阴谋,各自安好,相安相生,才对他人产生善意之情感。
城邦政治生活的文明化,是高贵的德性引导下的法治化之结果,传统英雄时代对勇敢德性的敬仰,转变成对正义与友爱德性的追求,勇敢也从“英雄”的“勇猛”转变为“公民的勇敢”。[43]所以,古希腊德性之文脉,如果我们粗线条来描述的话,实际上就两种类型,从神话史诗所歌颂的诸神所代表的永恒的自然天道向英雄美德的过渡,从英雄美德向城邦文明的公民美德过渡。英国历史学家C. M. 鲍勒(C. M. Bowra)对古希腊的市民美德做了这样的评论:
在贵族制和贵族的统治下,城邦达到了比较大的政治稳定性,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这是把古希腊真正与周边邻国区分开来的东西。即便在漫长历史之后,贵族制失去了它的强势,但城邦作为人类所欲求的有价值生活的可能形式的体现,依然保持为希腊人国家观念的核心。贵族制主张,它们的优先地位建立在诸神的厚爱上,因此相信,“它是善的”。对他们而言,“是善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也仅仅只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伦理概念,“成为善”或者说具有美德,是万事万物内在具有的一种本质上的卓越性。凯俄斯(Keos)的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大约公元前556—前468)写过,一个好人就是“举手投足和心智,全有教养,毫无瑕疵,真正的高贵”。
与此理想相对应的就是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出于最紧密的相互关系而注重声望。一个男人,就是具有自我担当精神而发展出自己最佳品格的人,并因其品格而被承认。因他为人处事的品格受到赞美,是成功的标准。但成功不只是一种对个人的承认,而且是对城邦的一种义务。一个男人为了其城邦的荣誉而死,就是一个好人。人们对一个男人的期待,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遵守法律,不做任何有可能损害城邦的事。他应该是审慎的,能够向他的祖先和他的教育证明自己是受尊重的。在如此“善的”观念中,除开很少一点道德德性的含义之外,主要是社会的德性。尽管如此,在道德上犯错对于一个男人和他的等级而言都是感到羞耻的事,道德德性依然有其重要性。贵族制的男人理想是深远而辽阔的。“为善”(Gutsein)不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生活领域,而且质朴地要求,一个男人要在每一种关系中证明自己是男人。[44]
之所以需要这么大段引用,是因为哲学家们一般都比较相信历史学家的描述才具有生活史意义上的真实性,通过这种具有真实历史性的描述,我们才能相信,伦理文明与制度文明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伦理文明为制度文明提供道义理念,使得规范本身具有道义基础,而制度文明才真正使得道义理念落实为有效的规范,从而进入实存,为道义赢得实在性。在这种正向促进关系中,哪里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哪里的生活就能实现出伦理的道义性,因而人的德性品质也能相应地获得提高。对于古代文明而言,贵族制是最好的城邦制度,它的理念和制度都以德性而目标,因而确实是通过贵族制,古希腊人达到了最高的伦理文明。在这样的伦理文明中,每个人按照城邦礼法不仅追求个人的德性品质的优卓,而且因德性品质的优卓取得社会的声望、地位和权利。因而城邦和个人在德性观念上是完全成为一体的,个人为城邦做贡献,尽义务,担责任都被完全视为自己分内的事,公共德性于是成为个人德性的标准。这固然与神话史诗对正义、友爱、英勇等社会性德性的弘扬相关,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落实到了城邦制度中,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者,体面、声望和荣耀对于古代的“熟人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又成为一个人在城邦中获得地位和成功的标准,那么必然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但贵族制有其内在的不可解决的困境,就是名门望族之间结成利益集团,从而在政治上向“寡头制”发展,于是就必然会破坏城邦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真正实施贵族制的德性原则,法治就难以实现,寡头之间的利益冲突,贫富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断地造成社会的动乱和不安。因此,希腊政治文明不可避免地在朝向民主制度的方向前进,但古希腊的伦理与德性在经历了智者运动的启蒙教育之后,引入了一种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它强调实用、竞争和成功,但通过修辞、论辩训练理智之优秀,通过音乐和诗歌陶冶灵魂之高贵,这样的精神在平民阶层也获得了发展。所以,这也是希腊城邦在伯里克利时代取得了民主改革的胜利,造就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繁荣之后,在伦理精神领域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人文主义转向。在这一插曲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亚里士多德在伦理精神上依然更多地保守着贵族精神的纯粹美善价值和高贵德性理想,但毕竟亚里士多德是个注重经验与科学的哲学家,在政治上他强调法治与平等,因而个人德性之卓越与城邦正义之伦理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中上升为普遍的存在原理,由此不仅将希腊文化推向了文明的最高峰,也开启了希腊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
但希腊伦理精神上的贵族主义与政治正义的平等主义,在希腊民主制下由于无法将民主制内在要求的普遍的个人自由确立为城邦伦理原则,正义伦理就只能以城邦秩序和公民幸福为目标,而不平等的秩序最终不仅将已经兴起的个人的无限自由人格损害得最深,而且成为城邦文明最后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古希腊城邦文明解体之后,德性文脉在希腊化时代之后,就完全转化为个人灵魂的修行,自我救赎的快乐和无纷扰的安宁,成为个人德性的标志,灵魂的过分自制也就开启了德性论向义务论转向的先河,古典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败呼唤新的神灵降临。
[1] 以下凡引《理想国》中文版,均不再注明,都是引用郭斌和、张竹明翻译的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只有在对译文略有修改时,才注明德文施莱尔马赫翻译版及其页码,即Platon: Der Staat, in: Platon Werke, Band III, in der übersetzung von F. D. Schleiermacher,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85, S. 315。
[2] [英]杰弗里·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页。
[4] [英]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册),晏绍祥、陈思伟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页。
[5] [英]伯里:《希腊史》(第一卷),陈思伟译,晏绍祥校,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9页。
[6]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页。
[7] [美]安东尼·朗:《心灵与自我的希腊模式》,何博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8] [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30 页。
[9] [德]奥托·泽曼:《希腊罗马神话》,周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以下凡引此书,直接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10] [英]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彭基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1] 参见拙著《道义实存论伦理学》第二章第二节“西方伦理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与伦理的普遍性”,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101—102页。
[12]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13] [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
[14] 参见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15] [英]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 年》(上册),晏绍祥、陈思伟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页。
[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
[18] [英]杰弗里·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年版,第9 页。
[19] [英]伯里:《希腊史》(第一卷),陈思伟译,晏绍祥校,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0页。
[2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页。
[21] [英]伯里:《希腊史》(第一卷),陈思伟译,晏绍祥校,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18—219页。
[22] 希波战争,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城邦抵抗东方波斯帝国入侵和征服而进行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第一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492年,第二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480年,第三次入侵发生在前479年,直到公元前450年,希腊军队再次取得海上和陆地的战斗胜利,才以波斯的最后失败而标志战争的结束,雅典成为海上霸主,而波斯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23] [德]爱德华·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下),余友辉译,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678页。
[24] [英]伯里:《希腊史》(第二卷),陈思伟译,晏绍祥校,吉林出版集团2016 年版,第443页。
[25]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51 节的笺注,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2页。
[26] 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Humanismus,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10, 11. Auflage, S. 46.
[27] [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陈中梅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8] [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陈中梅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
[29] [英]M. I. 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48页。
[3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31] 括号里的数字是《伊利亚特》的“行”数。
[32] [美]大卫·博罗廷:《奥德修斯的诸种关切》,温洁译,载《荷马笔下的伦理》,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3] [英]M. I. 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54—55页。
[34]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28页。
[35]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10—11页。
[36] 在本通史导论卷《道义实存论伦理学》第二章对此已经做了诠释,这里从略。
[37] [英]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3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页。
[3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页。
[4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页。
[41] Aristoteles: Politik, übersetzt von Eugen Rolfes, in: Aristoteles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in sechs B.nden, Band 4,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95, S. 138.
[42] Aristoteles: Politik, übersetzt von Eugen Rolfes, in: Aristoteles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in sechs B.nden, Band 4,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95, S. 140.
[43] 亚里士多德说,勇敢作为一种美德,是胆怯和鲁莽这两种极端性格的中庸,《荷马史诗》以刻画狄俄墨斯和赫克托尔来歌颂这种美德,但无论如何,作为英雄的德性,它总是与英勇杀敌甚至嗜血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它的始因是为了荣誉、体面、怕被人耻笑等等,都很难真正与勇敢美德的特征相等同,最接近于勇敢之美德的,是“公民的勇敢”,它面对的敌人大多不再与自己无关、可能只与“国家”或“政治”相关的“敌人”,而是自己惧怕法律的惩罚,怕丢面子以及为了奖赏等,所以只有公民勇敢的始因才是追求真正品行的高贵。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注释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127页。
[44] C. M. Bowra: Griechenland. Von Homer bis zum Hellenismus,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Hamburg, 1972, 1974, 1975, S. 54.
http://philosophy.fudan.edu.cn
philosophy@fudan.edu.cn
021-65642731
200433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光华楼西主楼2308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