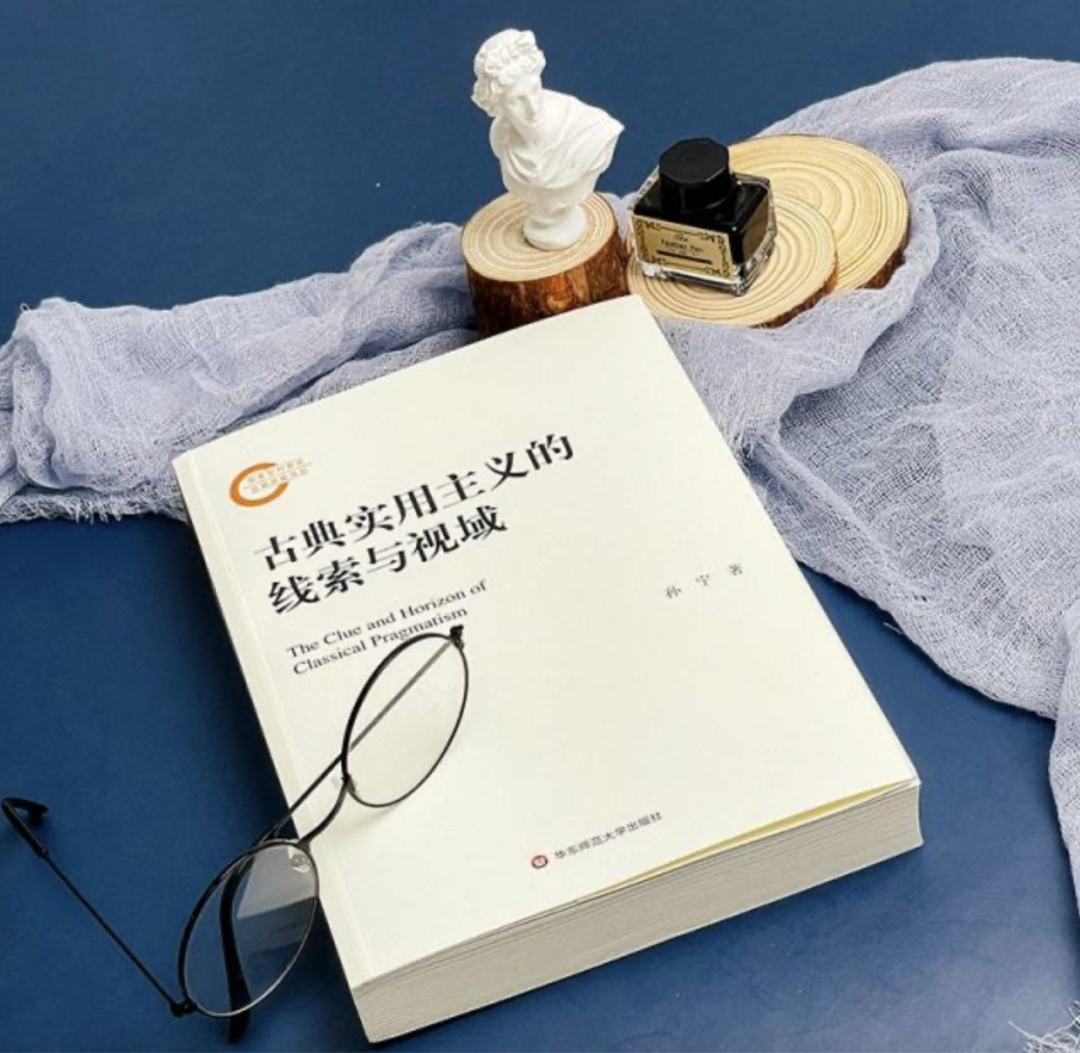一种可能的世界观
(孙宁)
我在导论中指出,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 “方法-体系-世界观”的整体视域中考察古典实用主义。作为一本哲学著作,本书的讨论主要是围 绕方法和体系展开的。现在,在这些讨论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去试着理解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被何种诉求所驱动,体现了何种思想特质,又落脚于怎样的精神视域中。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指出:“较之于其他文明世界中的国家,美国对哲学的关注更少。美国人没有特有的哲学流派,也极少关注与之竞争的欧洲流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美国人民在理智探究中几乎都用到了统一的方法和规则。因此,虽然嫌麻烦没有去定义这些规则,但他们毕竟还是拥有一种哲学方法。……美国人不需要让书本教会他们哲学方法,他们在自身中就能找到。” 尽管美国是否有特有的哲学流派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托克维尔非常敏锐地把捉到,有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从根本上规定着美国思想的表现形态。
我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存在一些可以将实用主义和其他哲学思潮区分开来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规定了实用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建筑形态,甚至超出了哲学理论的界限,深刻影响着美国思想的其他各个层面。詹姆士将这种总体性特征称为 “气质”(temperament)。他告诉我们,一种理论的气质或者是 “刚性的”,或者是 “柔性的”。但我们不能忘记, 气质的拉丁语 “temperamentum”原意为按一定比例和关系的混合。任何理论气质本质上都是一种混合气质,这一点在实用主义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用詹姆士的话来说,实用主义 “可以像理性主义那样具有宗教性,也可以同时像经验主义那样保留与事实的最丰富的亲密性”。或者说,它可以是 “刚性和柔性的中介”。
较之于 “气质”这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我更倾向于用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 “世界观”(Weltanschauung)来指称这些支撑方法和体系,并在哲学的分析和论证中得到体现的总体性特征。为了说明 “方法/体系”与 “世界观”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 “作为概念的世界观”(Weltansicht)和 “世界观”(Weltanschauung)之间做出的区分:“作为概念的世界观”必须在语言中获得意义,它是语言的产物,并通过语言发挥自己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概念的世界观就是语言共同体本身;而 “世界观”则是被意识把握的世界,它作为一种整体性经验规定了世界的本质以及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它并不受限于语言,而是从本质上规定了语言。根据这一区分,尽管我们必须通过 “作为概念的世界观”来探讨 “世界观”,但 “世界观”在更深的层面规定了 “作为概念的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形态。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实用主义的 “世界观”(world view)应该被更确切地称为 “世界感”(world sense)。因为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导论和具体讨论中所阐明的,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中,离开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等其他感觉形式的纯粹观看只是一种无法成立的理论虚构。
正如洪堡所指出的,我们只能通过 “作为概念的世界观”来探讨 “世界观”,所以完整地揭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就意味着重述本书的全部分析和论证。这里只能概要性地指出几点。首先,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中,因为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中,所以世界观在首要意义上并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它意味着个体与世界的动态关系。世界观不是理性伪造的结构或模式,而是暂态的生命习惯,是生命进程中的踏脚点和脚手架, 它为我们的当下行动提供方向,又能根据新的经验而随时修正自己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不能被描述和分类,只能被不断塑造和拓展,它不是去被发现某个或某组确定的关系,而是去探索如何将一组关系引向另一组关系。在这个实验性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一切看似明确的结论和简单的归纳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
其次,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中,具有活力的世界观必须是一种开放和多元的世界观。这首先意味着向一切可能的经验敞开,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用主义者认为,尽管每个人最终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世界观,但世界观之间的批评、比较、讨论和交流总是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应该自闭于某个固定的理论框架,他需要的既不是机巧,也不是盲信,而是真诚的态度、反思的意愿、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责任感,以及向一切经验讨教的态度和意愿。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根据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对世界的分析和综合必须以生命实践为导向,理论分析的结论同时必须是生命活动的结果,哲学的思考必须落脚于真实的生命语境。实用主义者的根本洞见是,缺少了对生命实践的关切,任何理论工作只会变成不健康的学术工业。詹姆士告诫我们:“哲学家总是在黑暗中摸索,而那些正在生活和感觉的人却知道真理。”实用主义者偏爱一切“活的”东西,并甘愿冒任何风险来保持这种活性。杜威在1904年佛蒙特大学的毕业讲演中区分了两种哲学:一种哲学致力于建构体系,另一种哲学则 “以工具性哲学而非最终哲学为 目标。所谓的工具性并不是要建立和保证任何特殊的真理集合,而是要提供观点和可用的观念,这些观点和观念或许能澄清和阐明实际而具体的生活过程”。实用主义者所倡导的无疑是后一种哲学。
以上几点已经在本书的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揭示,在这里重提它们的原因是,我在研究过程中和它们产生了切己的共鸣。通过研究他人的世界观,我们也在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在了解他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塑造自身。思想研究的最终价值与其说在于被研究者,不如说在于研究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帮助要远比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贡献来得重要。
我的博士阶段学习是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和美国杜威中心度过 的。南伊利诺伊大学有着深厚的美国哲学研究传统。很幸运,在我读博期间,当时南伊大哲学系的美国哲学研究团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强的,其中包括专治杜威的希克曼(Larry Hickman)和亚历山大(Thomas Alexander),专治皮尔士的安德森 (Douglas Anderson),专治清教传统的史提克 (Kenneth Stikkers),专治罗伊斯和过程哲学的奥西尔(Randall Auxier),以及专治新实在论的曼弗雷迪 (Pat Manfredi)。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参加了每位老师开设的全部研讨班,并参与了杜威中心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杜威课堂笔记、杜威书信集和罗伊斯标准版文本的编订工作。我的博士导师希克曼教授还花了三个学期的时间和我一起重读了詹姆士和杜威的几部关键著作。这些良师是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我从他们那里习得了让我终身受益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方法。他们不仅是美国哲学传统的细致解读者和有力推进者,还对学术保持着极大的热忱和敬畏。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从原计划的两个小时延长至半天的 “研讨班”,五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就几个关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让本该画下的句号变成了无限延伸的省略号。除了南伊大哲学系的诸位教授, 我还在不同场合向美国哲学促进会和欧洲实用主义协会的各位教授求教过关于实用主义的种种问题,受益良多,无法在此一一尽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伊利诺伊大学还组织出版了著名的 “在世哲学家文库”(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该系列由谢尔普(Pual Arthur Schilpp)于1939年创立,他一直担任编辑至1981年,之后由汉(Lewis Edwin Hahn)、奥西尔、安德森和比尔兹沃思(Sarah Beardsworth)相继担任主编,至今已出版30余卷。谢尔普最初的构想是让仍然在世的杰出哲学家来澄清自己的思想。该系列的每一卷都收录了其他哲学家和主要研究者对某位杰出哲学家的批评,该哲学家分别对此做出回应,并专门撰写详尽的思想自传。除此之外,该系列还收录了完整的参考文献、有学术价值 的照片和手稿样张等。事实证明,这个文库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谢尔普的预期,甚至成为这些杰出哲学家的核心著述。近年来,随着各位教授的相继退休和因为种种原因的离职,南伊大哲学系的美国哲学研究已经不再有当年的气象,而位于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杜威中心也在2016年因为经费等问题而停办。所以,本书除了致敬,更多地还是一种纪念和缅怀。
中国的实用主义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就已传到中国,并和刚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对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起过重要作用。后来由于中国出现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误会,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实用主义研究也由此长时期停顿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改观。从80年代开始,以刘放桐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开始了实质性的交流。1988年,中国哲学界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实用主义讨论会,就如实评价实用主义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与此同时,涂纪亮、王守昌、车铭洲等前辈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实用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国内的实用主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0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于2014年改名为复旦大学杜威中心)。至此,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上可以说全面恢复了。在回国进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工作之后,我就一直在参与杜威中心的工作。在陈亚军教授的带领下,这个因为实用主义研究而凝聚起来的学术共同体不仅汇聚了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各位前辈老师,还吸引了许多在学术事业上满怀热忱的同道学友。我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也很荣幸能够为之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各位师友那里受益良多,虽无法尽数,但心怀深深的感恩。没有诸位师友的帮助和激 励,本书是无法完成的。同时也要感谢哲学学院为我提供了极为舒适的环境,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最后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王海玲老师,她细致认真的工作实质性地提高了书稿的最终品质。
本书的一些章节曾以不同的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或在会议上宣读过。上编中讨论桑塔亚那的一章是我硕士论文的主体部分,之所以将它收入本书,一方面是出于历史性的兴趣,更多地则是为了纪念我的硕士导师汪堂家(1962-2014)先生。在这一章中,除了增加的 “引言”,我只做了极少的改动,因而也就保留了很多不成熟甚至幼稚的痕迹,特此说明。
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获得了无上的乐趣。阿伦特曾将本雅明(Walt Benjamin)比作深海采珠人:“他知道,为了打破传统的魔咒,没有什么方法比将那些 ‘丰富而奇怪的’东西——那些珊瑚和珍珠——从被传承下来的一整块坚石中挖割出来更有效了。”本雅明相信,那些曾经鲜活之物会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一些永恒的结晶,它们沉积在海底,等待采珠人将它们带到当下的世界中来。本书的工作与本雅明的工作并无二致。但不得不承认,碍于学力,我的勘探和挖掘工作并不完善,很多时候也没有对手头的材料做恰当而充分的雕琢。因此,本书仅仅是我个人研究实用主义的 一个阶段性总结。但无论如何,实用主义这种 “丰富而奇怪”的思想值得我们进行反复的勘探和挖掘。“尽我所能,但不如我所愿”(ut potui, non sicut volui),这是中世纪的抄书匠经常在工作结束时题写的句子,出于同样的想法和心情,我把它放在本书的最后。本书中的一切不妥及讹误之处,本人应负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