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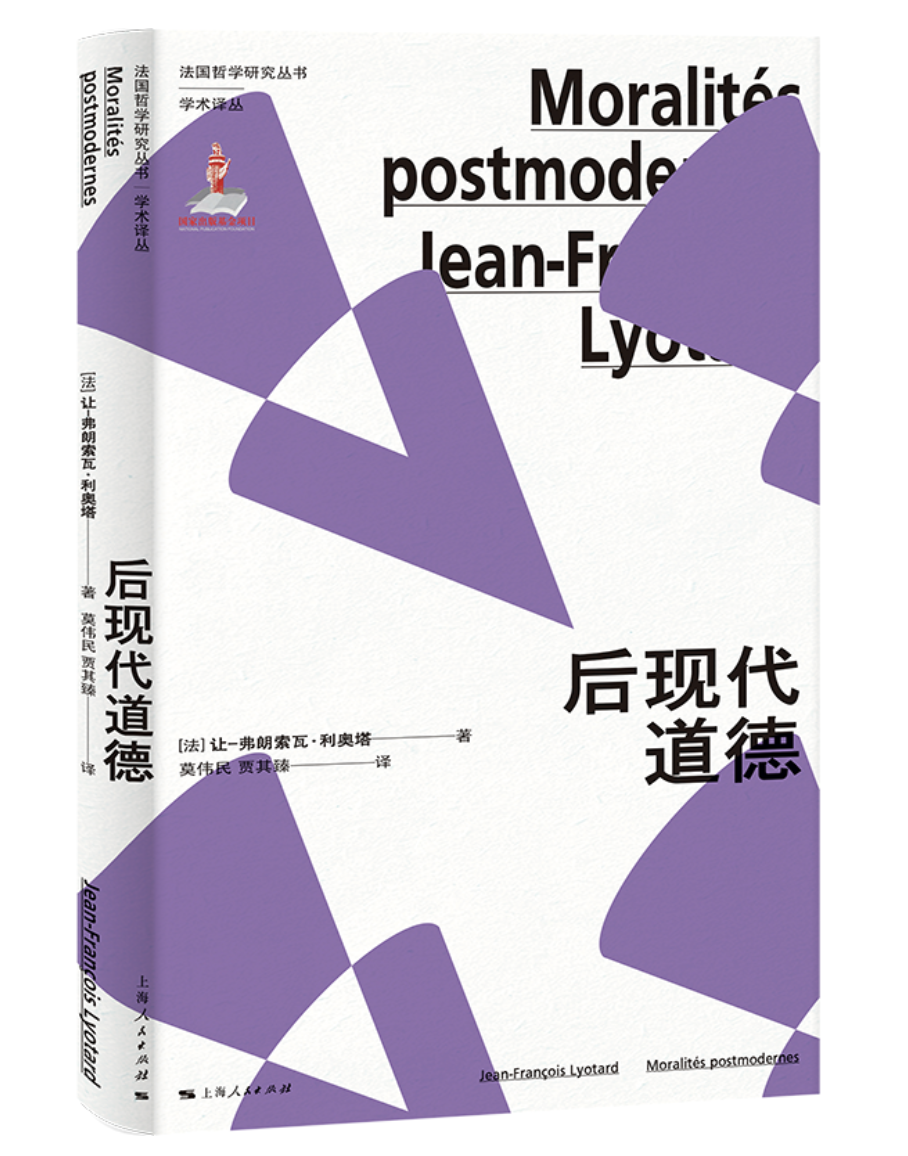
作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译者:莫伟民 贾其臻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4年2月
《后现代道德》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伦理学专著。利奥塔没有专门探讨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权力、道德义务等道德领域的重要问题,毋宁说他的后现代道德是在宽泛意义上的“行为准则”,而且这样的行为准则并不具有实践理性的普遍有效性。
利奥塔选取“流变”“市场”“速度”“信息”“资本”“多媒体”“制度”等主题,聚焦“文化市场”“大都市”“想象博物馆”“平面艺术”“无声音乐”“海湾战争”“后分析哲学”等问题,力图反映文化人、艺术人、媒体人、政治人、哲学人的后现代行为准则:坚持异识。
快速变化的后现代社会并不妨碍人们再现生活、享受生活。所谓后现代道德,就是一种“审美的”快感。利奥塔试图让读者以充满好奇、焦虑、惊讶、惊叹的儿童心境去阅读后现代传说,从而设法改变以往那种追求清晰严密的哲学写作方式。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著名法国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现象学》《话语,图形》《力比多经济》《后现代状况》《后现代道德》《异识》《海德格尔与犹太人》等。
莫伟民
莫伟民,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担任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法国哲学研究和译丛”主编、《法国哲学研究》辑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法国哲学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福柯思想、西方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等。已出版《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二十世纪法国哲学》《莫伟民讲福柯》《战后法国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等各类著作十余种。
贾其臻
贾其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23届硕士研究生。
总序 哲学经典翻译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事业/1
译者前言 流变、制度和异识: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思想/1
引 言/1
赘 言
1. 玛丽在日本/5
2. 市郊结合区/16
3. 图形设计师的悖论/30
4. 有趣/ 有利吗?/43
制度的幻想
5. 围墙、海湾和制度/59
6. 后现代寓言/71
7. “地上本没有路”/86
隐 匿
8. 总路线/97
9. 奇怪的同伴/103
10. 仆人指南/122
11. 可能的纪念碑/133
地 穴
12. 不知不觉/151
13. 恐惧是内在的/161
14. 音乐,无声/175
15. 最微小的灵魂/190
原始出处/202
后现代就是处在现代之中重写现代!
文:莫伟民
本文节选自
《后现代道德》“译者前言”
(注释从略)
后现代就是处在现代之中重写现代。现代性有不少特征,但利奥塔在重写现代时似乎最看重其中两个特征:历史性与元叙事。历史性就是关于时间的现代想象。现代性作为现代的时间性,意味着有可能且必须与传统决裂,并确立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在西方哲学和文化领域,一旦出现了历史性概念,就告别了前现代而进入了现代。理性进步、自由解放,以及人类得到科技拯救等“元叙事”也是现代性的标志。而历史性概念一旦丧失,元叙事也随之被小叙事取代,西方也随之从现代进入了后现代。现代性有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之分。重写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也就有了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道德。但利奥塔强调后现代并未摆脱、抛弃现代,因为后现代已经在现代之中了,后现代是现代的组成部分。作为重写,其与原版不同,后现代性只是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性,故此,后现代道德只是通过重写而不同于现代道德的另一种道德。
利奥塔重申知识具有的唯一的但可观的合法性就是使道德成为现实。这充分说明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具有道德维度,包含了一种后现代道德。当然,利奥塔并未专门撰文来集中阐发道德学说,他的后现代道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文集《后现代道德》《异识》和其他有关著述、访谈中。即使在《后现代道德》中,他也并未像以往哲学家那样提出一种道德学说,并未专门探讨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判断、道德权利、道德义务等道德领域的重要问题。他的后现代道德思想主要散见于他对文化、审美、制度和发展等主题的见解之中。或者说,利奥塔在此使用的“道德”一词是宽泛意义上,类似于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的“行为准则”、行为规则。从伦理上讲,“有必要”不是伦理的,“应该”也不是伦理的。必要性并非义务。因此,这样的行为准则显然不具有实践理性的普遍有效性。利奥塔认同列维纳斯的观点:普遍主义道德命令是空洞无效的。
《后现代道德》由15 篇文章和访谈构成,是文集,而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专著。行文注重审美式的描写和叙述,而不是逻辑论述和推理。选取“流变”“市场”“速度”“信息”“资本”“多媒体”“制度”等主题,聚焦“文化市场”“大都市”“想象博物馆”“图形艺术”“无声音乐”“海湾战争”“后分析哲学”等问题,力图反映文化人、艺术人、媒体人、政治人、哲学人的后现代行为准则:坚持异识。利奥塔试图让读者以充满好奇、焦虑、惊讶、惊叹的儿童心境去阅读后现代传说,从而设法改变以往那种追求清晰严密的哲学写作方式。我们接下来不妨领略一下该书的主旨概要。
利奥塔看到:林林总总的道德通常形成鲜明对比,快速变化的后现代生活使所有道德化为乌有。生活并不妨碍人们提出问题:如何生活?为何生活?生活全方位发展,生活有各种意义。人们再现生活,把生活的所有意义炫示、展现给各种各样热爱生活的人,并享受生活。关于所有道德之道德,就是“审美的”快感。于是,利奥塔关于后现代道德之道德也就是后现代审美。
后现代知识不仅精炼了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还增强了我们对不可共度性的承受能力。利奥塔不仅在艺术和绘画领域与梅洛-庞蒂、克利、塞尚等人分享审美感受性,还与德勒兹一起受惠于弗洛伊德思想,设法用“利比多流变”“脉动装置”“能量交换器”等概念来取代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摆脱同一性逻辑的束缚,哲学也就变得非哲学化了,形而上学也就衰落了,艺术也许成了救赎之路。
在利奥塔看来,在后现代社会,文化同资本一样成了商品,出现了文化流、资本流和文化资本流。文化资本指的是:所有文化都在文化银行里变成资本。文化银行是人类的存储器,它必须使每个分行饱和。知识分子既不是资本的拥有者,也不是资本的管理者。知识分子签合同著书,知识分子被当作微不足道的文化劳动力而被剥削。知识分子,一半是受雇佣者,一半是手艺人。知识分子既感到舒适,又感到艰难。因为,知识分子不能老是兜售同样的东西,必须创造、阅读、想象,否则就会招致雇主的不满。与知识分子一起从事文化商品生产、销售、流通、配置的一切人员都是文化资本的小小流变。词语、难懂的短语、音乐、图画、文雅举止都是一些文化流变。展览会也是文化流变,博物馆是所有流变的目的地。博物馆需要特异性来充实。最好的流变最快到达,妙不可言的流变刚出发就到达。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实时或电台和电视中的现场直播般的时间。但更好的做法,就是在流变到来之前,去预测流变的来临和“实现”。这就是信贷货币。这是贮存的时间,先于实时而被花费。人们赢取时间,借取时间。时间是金钱,金钱是时间。而书写太缓慢了,人们必须购买文字处理系统来生产文化,这样快速流变的文化被利奥塔斥责为便当文化。利奥塔则欣赏思想水潭之真实的缓慢流淌,“真正的流变是地下的,在地下缓慢流动,形成水层和源头。人们不知道它们会从哪里出来。它们的速度也未为人所知”。
利奥塔抗拒美学在文化的名义下被发展所吞并,文化作品被商品化,共通感被转化为共识,人类智慧被商业化。利奥塔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现代文化唯利是图,讨论会、访谈、研讨班都是为了谈论同一件事情,谈论相异性(l’altérité)。大家都一致认为共识是可疑的。人们追逐相异性,光顾小型的流动文化市场,崇尚文化资本的美妙的小小流变。文化资本主义所发现的,就是奇特性(la singularité)市场。每个人都说明其奇特性。每个人都是在他所处的性别、人种、语言、年代、社会等级和无意识构成的网络中的位置来谈论自己的奇特性的。我们已在文化世界这个博物馆中拯救和贮存了金字塔、兵马俑等文化遗产,现在必须对当代的一切,无论是作品,还有生活方式、隐语、美元汇率等都进行存档。
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信息产业已取代工业社会的传统产业,巨城可以无拘无束地拓展。大都市的边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外拓展。有城墙环绕的城市变成了大区域,郊区变成了新城,巨城就没有城外和城内之分了。“远程通讯和远程生产不需要构思精妙的城市。巨城环绕着从新加坡到洛杉矶和米兰的行星带。整个区域介于虚无与虚无之间,撇开了实际经历的延续和距离。每个栖所都成了一个住所,这个住所中生活就在于传送和接受信息。”一些西方国家凭着巨城来实现和推广其虚无主义。西方国家把这个虚无主义称作发展。在唯美的巨城中,哲学家处于或迷失于注意或留意作为绝对的虚无这样的境地。这个境地够滑稽,哲学家构造体系,又推翻体系,努力去奠基、思考常常肆虐的虚无主义,既展开又遮掩这种虚无主义。应该拒绝美学巨城的诱惑,默默抱怨绝对所缺乏的一切。但是,利奥塔反问:作为巨城中的生存方式,被调节的美学,真的“显明并隐藏了”绝对的一种缺失所具有的痛苦吗?或者,这种痛苦难道只是一种虚构,哲学需要这种虚构来使哲学归于自己的角色合法化吗?当近日哲学家或作家或艺术家坚持要听取自认为听到在该风格的弱音器上鸣奏的绝对的缺失时,他们疯了吗?集合城市(la conurbation)这个怪物在普遍化审美这点上与后现代哲学家相遇。
虚无主义不能保持为思想或论题的一个对象,虚无主义影响了作为哲学话语关键的辩证模式。虚无要求思想记录虚无,不是把虚无记录为其批判论证的产物,而是记录为其反思写作的风格。哲学家在“审美”时,不能偿清这笔风格债。与尼采或海德格尔相比,维特根斯坦、斯坦(Gertrude Stein)、乔伊斯、杜尚(Duchamp)似乎具有更好的“哲学”头脑,因为他们更适合于考虑毫无出路的虚无,更具有自己的风格。正是因为风格的事情,哲学在今日才受到争论、威胁,既得到尝试又受到怀疑。文化操纵着发展(包括文化的发展)的欲望,而不是正义、平等或命运的欲望。大众传媒向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审美的种种巨大可能性。而由巨城的文化机构提出来的那些角色的相互竞争的多元性,对这种文化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多重的审美化趋向把我们的文化变作一个博物馆。当对象失去了其作为对象的价值时,只有用来展现对象的“审美方式”保留了价值。“风格”成了价值,移情发生在风格上。“审美是巨城对因缺乏对象而产生的焦虑的反应。如同文化机构,巨城所特有的博物馆也是一种郊区。在这家博物馆中,所有文化都悬置在它们的别处与我们的此处之间,我们的此处本身就是早已消失了的它们的此处的别处。”但这种博物馆式审美必须遵守想象律,应该使人感兴趣,应该提供好、坏、爱、恨这样的方式、风格。在审美领域中,当商业占有崇高时,商业就会把崇高变成嘲笑。更不存在崇高的审美,因为崇高是一种情感,它从审美的无谓中获取其苦涩的快感。现在不是哲学家打算建造一个思想巨城的时候,哲学家无需依据共同体来进行思考,也无需加入一个无论什么样的政党。
利奥塔断言,科技的发展已变成一种加重不安而非减轻不安的手段。我们不能再把这种发展称作进步了。发展似乎通过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自主的动能而继续自己进行下去。发展并不答复产生于人类需要的需求。相反,个体的或社会的人类存在的稳定性似乎始终被物质上、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发展的后果及其结局所破坏。科技世界对每件物品都加以复杂化、传播、数字化、合成并强行修改其尺寸,这根本无关于我们对安全、身份、幸福的需求。发展并非人类的一个发明。人类是发展的一种发明。人类不是发展的动力,人类不应该把发展与意识和文明的进步混为一谈。人类是发展的产品、工具和见证。即使人类对发展及其不平等、不规则、明定性、非人道所提出的批评,也是发展的表现并有助于发展。
利奥塔谈论有关图形设计者(le graphiste)的悖论。由于受到多种束缚,图形设计者只能在很狭小的自由运动空间中活动。作品要迎合读者、观者,要讨人喜欢,要显得有说服力,要显得恰当合理,作品要忠实于自己所指望的制度、展出等,忠实于其字面现象和精神。这些都是对作品的束缚。说白了,就是作品要愉悦观者的目光,使眼睛获得快感。作品并不使思想去认识,而是使思想去享乐。在旨在获得这种快感时,作品就在美学一边了。艺术家、律师、证人、传记作者甚至法官都是图形设计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解释,他们都是解释者。解释是解释学艺术,也许是最难的一门艺术。他们知道这样一些规定:不要给被解释的事情添油加醋,不要让被解释的内容自相矛盾,不要忽视以前的解释,不要把一种解释强加为确定无疑的。图形设计者通过设计情节,告知主体所指望的事情。精美的电影广告填满了大厅,赏心悦目的企业徽标在引人瞩目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可用于贸易、商业、消费,并将加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图形商品像其他商品那样流通。无论商品是文化商品并具有公共或社会旨趣,还是具有私人的用途和旨趣,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凭着一幅精美的图形作品,浪费的那点时间,通过商业成功或声誉,使得幸运的所有者或者被指望的“物品”的经营者赚取大钱。
图形设计者们要依靠公众才能生存,而公众是暂时的感受性的不停拆散和重组。当然,公众也有常项,传统的语言、某个观念甚至无意识观念,可确定的生活、就业、经济增长和衰退等状况,就是公众的常项。图形设计就是要确定这些组分之间的比例,使公众感到惊奇,让观者看到出乎意料的一切。然而,由于当今社会有许多动机是不确定的,许多动机是不可预见的,因此,图形设计者的艺术就有危险了。虽然有危险,但图形设计者们还是有章可循,尽管这种规章是事件的规章。作为现代都市的艺术,图形设计专门依赖于文化的、商业的、政治的和实用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接受相同的量体裁衣,都遵守相同的无规则之规则,事件的规则。图形设计是一种现代艺术,旨在通过设计情节而使人感到惊奇。行人驻足不前,仔细观看广告,接着去看演出。图形设计者所签合同规定作品应该指望事物。于是,图形设计者的悖论就产生了:他愈把自己掏空任凭事物来栖居,作品就愈忠实于它所指望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