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郁喆隽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1.12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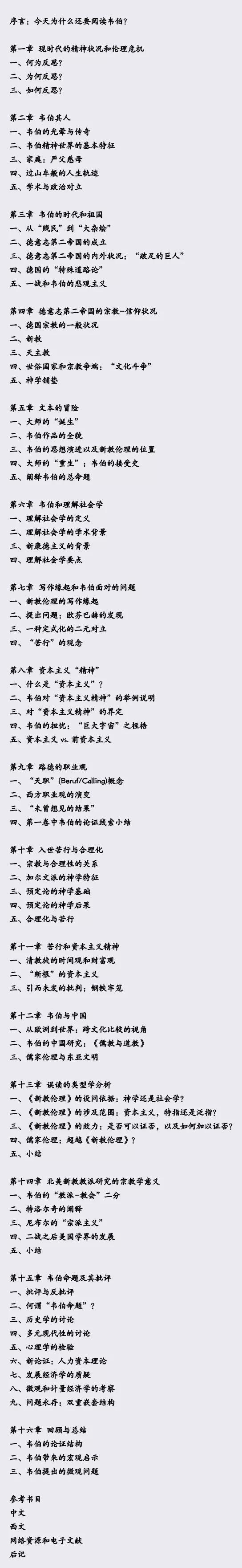
不要因为一本书的盛名而去读它。“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读书首先要明确的是为己还是为人。这里的 “为己”不是指自私自利的逐利行为,而是为自己找寻安身立命的根基。这里的“为人”也非舍己为人的利他行为,而是以一己之学问解他人的困惑。本书是对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的研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写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作品。它是一部以“为人”的姿态、做“为己”学问的作品,而其“为己”的结论又成为投身“为人”的起点。可以说韦伯既是自己学术写作的作者,又是自己学术写作的读者。作者和读者之前产生了一种角色互换与共鸣。
人文学者天然地容易陷入一种学科的“祖先崇拜”——即将历史上的经典奉为圭臬,甚至将之上升到神圣而且不容玷污的信仰地位。本书并不打算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经典解读路径。文本的意义在作者写作完成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仅仅属于作者本人了。后世的阅读和阐释也构成了本文意义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对读者而言,文本的意义不是深埋在地下的矿藏,它并不是现成的、不变的。发现自身与文本之间的“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韦伯术语),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种价值关联能跨越时空的鸿沟,克服文化的差异,使得经典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身上获得重生。对韦伯来说,这种重生所反映的也许主要并不是其作品本身的伟大,而是读者及其时代的困顿。
所以在这个序言中,笔者并不打算像很多导论一样,使用太大篇幅来赞扬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贡献,而是要谈谈今天我们为何还要阅读韦伯。韦伯的新教研究对于当下的我们还可能有什么意义。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或许预示着我们自身深陷的问题。因为,所有阅读都是反身性的。世界的大问题和个人的小问题休戚相关。
一、
今天的中国读者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在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中理解中华文明,并且要在全球化的框架中规划和憧憬中华文明的未来。然而,这一任务受到了很多进程的扰动,甚至其必要性也备受怀疑。
就世界历史意义而言,21世纪始于“911事件”。在此之前的近十年中,世界处在一种冷战结束后的乐观情绪之中。伴随着全球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中突然消失,笼罩在全人类头顶数十年之久的核战争阴云瞬间散去。对立似乎是以一方的不战而胜告终。于是有知识分子提出了“历史终结”(福山)的看法。而然“911事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观方式提醒着每个人,那种乐观情绪可能是盲目的。它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二战之后存在长达70年的“长和平”,是否还会继续几代人的时间?全球化在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量之后,是否会顺理成章地给所有人带来福祉?文化交流是否必然意味着文化融合?没有几年的时间,登上全球舞台的事件——从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冲突,到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都提醒着人们,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对立其实掩盖了人类更深层次的对立——文化、种族、宗教以及世界观。全球化的力量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弥合那些旧有的裂痕,反而加深了、甚至制造了一些新的裂痕。这里所触及的不仅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未来时遭遇的不确定性,而涉及人的自我理解和价值建树。当全世界看到ISIS这样的残暴组织时,不得不重新直面“现代性”的问题——现代为何制造出了如此的野蛮。当我们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立场时,人类的种种对立更多地呈现为地缘政治的冲突。然而当我们反躬自问的时候,地理和地缘的问题就转变到了时间轴线上。这种时间轴线并非物理意义上单向流逝的时间,而是赋予所有事件意义的历史时间。它不仅回望过去,还要指向未来。或者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惟有当它指能够向未来时,它才能回望过去。在迷惘中人们才发问。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就是这样一部世纪初的“困顿之作”。一个世纪之前,韦伯的祖国也面临着极为迫切的现代性问题。韦伯尝试从欧洲文明内部来为德国从何而来、现状如何,以及将往何处去的问题找到一个回答。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吊诡的概念。首先,现代的内核始终处在流变当中。它之所以处在流变之中,乃是因为我们身处现代性之中。也可以说,现代化作为一个进程尚未完结,仍在展开和进行的过程之中。即便是所谓的“后现代”,也是现代的一部分。对现代的界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人的自我认识。其次,现代是一个对照概念的一端。它必须要通过和“前现代”的对比,才能凸显出自身的现代性来。在此意义上,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现代人。甚至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商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现代的。而在他看来,那些依靠头衔收取地租的贵族是前现代的。现代作为一个思想史的概念,出现却非常晚近,而现代本身包含了一种元价值判断。正因如此,现在性不仅仅是关于过去,而且还具有未来向度。人因为有未来,因而需要回望历史。“历史”绝不是马后炮和吃老本。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冷战当中的现代性表现为对抗性。当这种对抗性消解之后,文化多元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在此,有必要区分两种文化多元:第一种文化多元是事实和描述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作为大航海时代和全球贸易的结果,这个星球上不再有遗世独立的文明。各个文明彼此知晓对方的存在,并或多或少认识到彼此在审美、道德、宗教乃至世界观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再也无法否认其他文化的存在及其实际影响。第二种文化多元是规范和价值意义上的多元。其基本假设认为,多元并存有助于各文明克服其自身固有的盲点,并在交流、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可能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来,人们应当欣然接受并拥抱多元的后果。现实当中上述两种多元混在一起,难以区分。后一种多元文化(论)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为基本框架建立起来的。然而,它没有预料到的是,事实上的文化多元可能导致带有强烈分歧的后果:一方面,任何形式的闭门造车和闭关锁国都不再是一个选项。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彼此产生了误解、嫉妒、怨恨甚至是仇视。这种负面结果不同于古代历史上的彼此仇视。它对本文化也会产生“腐蚀作用”。价值的多元未必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但在文化不再表现为均值的地理板块,而呈现为另一个模式:在单个国家的边界内,文化的连续脉络被中断,遭到质疑,文化均质被前所未有的打破了,甚至出现了深刻的内在文化裂痕。我们在激烈批判他者的时候,却无力评判自己。
任何文化都要回答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前一个问题可以用历史来加以解释,即在我们之前的世代经过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他们才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而我们有在何种意义上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局限和困顿,在何种意义上想要做出我们这一代的改变。但是在巨大的危机感面前,如果仅仅采取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立场的文化观,大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为何变成了这样,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然而它却无法告诉我们,未来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可以期许一个怎样的将来。这就是文化的“定位”作用。文化之定位如同为人划定坐标轴。有了定位才能定心。然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文化中一些理所应当的世界观和价值预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该文化中的人不能超越文化本位,就会产生出一种错觉来——认为这是该文化遭遇的独有挑战,也会生进而生发出一种特殊的困顿感甚至受害论来。不过,倘若能够跳出该文化的本位视角,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所有文化都遇到的挑战和困境——这就是现代性。因此可以说,文化能够给人带来确定性,也可以带来不确定感。文化自信需基于文化内省和外拓,而非盲目自大或自怨自艾。
二、
上一代的本国学者由于对庸俗物质决定论的抵触,而导向某种文化决定论。韦伯在特定的时刻被译介入汉语学术圈,因而被塑造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事实上,韦伯将社会科学界定为一种“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而文化科学则是属于“实在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的一部分。从这一科学建筑术来看,韦伯反对将文化单纯视为精神或者观念性的,文化也有其物质和制度性的维度。也不要忘记韦伯本人是从国民经济学转入对宗教问题的研究的。这一轨迹也足以说明,韦伯不是简单的“唯心主义者”,或者文化决定论者。文化既有其器物和制度安排的要素,也必定包含思想、观念的成分。换言之,韦伯的新教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不是仅仅是被本能驱使的动物,即便是要满足生理需求和欲望,也必定带有其思想和观念的深刻印记。正如韦伯研究者本迪克斯对韦伯思想的总结:没有理念的物质利益是空洞的,但没有物质利益的理念则是无力的。对物质利益的一味追逐本身并非自然而然,反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体现。当代的技术力量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具有惊人的潜力,然而它尚需要观念的引导,才知道如何将此潜力在哪个方向上转化为现实——犹如飞机发动机和导航设备的关系。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生的变化是极为深刻的。这场短时段的变化可以被视为19世纪中叶以来面对全球化冲击中的一个阶段——长波中的短波。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者们开始质疑冲击-回应模式的合法性,但是其对立面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多半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而忽视了物质世界的急剧转型以及当事人心态的动荡。这场长达两个世纪的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同时发生的:即一方面在观念和精神领域;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方式领域。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开创了一个范本,将欧洲宗教改革后产生出来的思想观念(新教的苦行伦理)和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桥接了起来。他采取的思路既是“唯物的”又是“唯心的”,或者说认为两者之间绝非简单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是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一视角(而非结论)对于理解本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有极大启示的。在当代中国的巨大断裂感背后,是否也存在着文化与现实传的连续性?这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还涉及规范-价值层面的追问:这究竟是一种赐福还是诅咒?
在长时段的现代性当中,中华文化受到的冲击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种冲击是全方位的,不止于思想观念层面,在某些层面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底。以下笔者感受到的一个例子:前几年,复旦大学有学生社团在上巳节这一天进行春日赏诗的活动。期间有学生身着汉服来参加,在和煦春光中,人面桃花相映,颇为风雅。其中也有男生穿汉服的,不过就显得不伦不类。一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经人点拨才恍然大悟——如今的男生不留发,不蓄须,穿着汉服总有一种太监的感觉。中国古人本来有“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念和世界观的价值判断,几乎不会有人质疑。而在现代化浪潮中,男士剪短发、不再留须。但这大多是出于卫生的和审美的考虑,而并非一件单纯思想观念的事务。如今自然少数人自然可以继续蓄须留发,但在旁人看来,其意义也已经发生了嬗变,成为单纯的个人审美喜好。
现代化的特征就是分化(differentiation),传统受到潜移默化的冲击、儒化和置换。某些传统可以恢复,某些却无法挽回,颇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受。人们的生活方式(form of life)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所以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经感叹,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74年)——这种感慨也绝非仅仅针对西来的坚船利炮,而又更深的观念冲击。在此前提下,一味地要求恢复传统,究竟是在追求空洞的认同感,还是追求文化的实质,值得深思。即便在外在形式上恢复一项传统(如汉服)并不困难,但也会遭遇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局面——传统从未一成不变,也将继续保持变化。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而吾辈更要反思变在何处、为何而变,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变局。
三、
欧洲自16世纪以来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积累的巨额财富,通常被归在“资本主义”名下。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认为,这种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并非主要由于一些外生的偶然机缘,例如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技术革新,或者内部阶层性剥削。资本主义诞生需要一种持续的内在心理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动力来源于宗教改革。韦伯身处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困顿之国。困顿使人思考。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没有直接关注19世纪的德国,其眼光与众不同:他首先采取了一种“退一步”的研究径路,向后跳越了三个世纪,来追寻西方资本主义的根基。其次,韦伯采取了“以人为本”的视角。这种以人为本不是指将人的利益和福祉视为根本,而是在社会认识论和行动理论上而言的——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看来,人的观念会对历史进程生产影响,思想、观念和世界观本身就是自变量,而不仅仅是应变量。因此在人文-社会领域中不存在所谓的“铁一般”的法则。处在外在的历史条件和机缘下,个体的人和集体的人(社团、民族、国家)依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韦伯的哲学根基上要破除历史主义的宿命论(也是虚无论),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一种能动理论。
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年代上有很大的重叠。这种有趣的重叠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张力的文化氛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方面笃信上帝,将个人救赎视为此生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个人也在努力寻求解放和自由,尝试从宗教的权威和以往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这种张力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他既不像以往的人那样彻底地跪拜在上帝脚下,也不像后来的人那样内心毫无敬畏,肆无忌惮。相比之下,当下的世人缺乏敬畏,甚至缺少对自身的敬畏,其决断会颇为鲁莽,其结果却影响持续久远。宗教改革虽然发端于信仰内部的不同理解,其动力截然不同于文艺复兴。但两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呼应。新教和天主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教所塑造出来的文化,从出世转向了入世。入世的信仰者一方面全然的接受上帝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另一方面不再将此世视为暂居之处,转而充分肯定此世生活的积极价值,并尝试在此世生活中彰显上帝的荣光。原本的对立和矛盾,在救赎的目标下被融贯了起来。财富成为了这一转变中的要害问题。欧洲的这一转型历经大约三四百年的时间。致力实业和商贸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而依靠传统地租和政治特权的阶层原地踏步。在德国到了19世纪下半叶,容克阶层甚至已然成为了德国进一步现代化的阻力。
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代人大部分国人并没有类似欧洲基督宗教的信仰,甚至就是无名的物质主义信徒,即便尚存一丝理想主义的色彩,也极少选择彻底弃绝财富的。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国人大致经历了欧洲三四百年中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最重要的是从以财富为耻到以财富为荣,甚至发展到了以财富作为衡量人和社会的唯一标准。换言之,财富成为了一种“救赎”,一种没有超越目标、缺乏实质内容的此世救赎。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致富,以及未来是否还能继续致富或者保有财富。于是这种救赎显得不那么牢靠,甚至是岌岌可危的。这种窘境迫使我们去思考人追求财富的深层动力:财富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说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人致富的心理动机是宗教上的救赎,那么如今我们致富的心理动力是什么?近年来,我国成为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重要市场。短期内致富之后,人究竟在追求什么?有人追求“面子”和排场,有人想要光宗耀祖,还有人寄希望于下一代。我观察到身边的不少人,是出于强迫(不得不)而去追求财富的。与其说他们追求的财富,不如说他们更加害怕贫穷。中国人的存款比例在全世界一直是较高的。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受到儒教文化的持续影响,还是由于缺乏周全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当代中国,在经历了一代人的财富“狂飙突进”之后,代际转换和承继的问题已经出现。改革开放的第一代致富者,都曾经尝过贫穷甚至饥饿的滋味。不过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后代得以摆脱了贫穷和饥饿。但是问题紧随而来,当人们不再是为了摆脱贫困积累财富时,当人们从未亲身体验过贫穷和饥饿的滋味时,这种动力是否还能持续?
四、
“资本”早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了每个人都无法忽视的物质性力量。即便不加上“主义”两字,“资本”也已经足以造成巨大的意义分歧。韦伯和马克思可以被视为研究资本主义的两个模本。不过要注意到两人的“时差”——马克思要比韦伯早出生大约半个世纪。然而两人研究的资本主义却相距了三个世纪。韦伯关注的资本主义在16-18世纪的欧洲大陆,而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主要在19世纪的英格兰。两人的对立并不是他们本身方法和结论的对立,而更多地是后世意识形态对立造成的刻板印象。马克思分析的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工厂,而韦伯考察的则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企业。而当1914年韦伯前往新大陆,亲眼看见了美国的当代流水线之后,他和马克思就构成了一个闭合的“框架结构”——两人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是一个连续统:韦伯(16-18世纪)-马克思(19世纪)、韦伯(19-20世纪)。可以说,韦伯本人恰好处在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上,资本主义逐渐在转变为一种非人的力量。马克思对此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尝试用人-人的社会关系,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但是韦伯在新教伦理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却有两个不同的切入点:一个显见的切入点是尝试从宗教根基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人-神关系对资本主义的塑造;另一个隐藏的切入点是一种对未来的担忧,即摆脱了宗教根基的资本主义,一旦和机械文明结合起来,将成为一种凌驾一切、宰制所有的非人力量。非人逻辑反过来控制人-人关系。这一点和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思路极为契合,后来也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
虽然我们不能幼稚地希望,资本主义重新扎根到宗教的土壤中去,但是依然可以发问:如果资本主义成为了颠覆性的力量,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再度驯服这头猛兽?可能对今天的人来说,需要担心的已经不再是往日的建构性力量——工商业资本主义,需要特别担忧的是金融资本主义。换言之,韦伯特别关注的是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根基。在他看来,勤勉、强制节约、反对奢侈、以荣耀上帝为目标的清教伦理最初才是形成资本的源动力。这也是所有一切其他现代合理性(rationalism)的起点。然而,单纯经济领域中的合理性推向极致之后,出现的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甚至是疯狂。那么谁将来遏制这种疯狂?
当今中国在绩效主义的驱动下,也沾染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一些个人信念迷惘、沉迷享乐和消费,整体道德水准出现滑坡,社会舆论撕裂……然而简单地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只是在回避自身的责任。关键是“我们”将如何做为?
救赎曾是“为己”的根本,而财富如今将“为人”和“为己”在基础上统合了起来。资本主义似乎成为了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无可撼动的制度。在个人的追求与挣扎,以及外在的、无法动摇的制度之间,似乎缺乏勾连。这道鸿沟令人绝望。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无可撼动的外在、非人之物,追溯到个人精神及其生活方式的根基。所以才讲,韦伯是在用“为人”之姿态做“为己”之学问。反过来,“为己”之发问又可以投身“为人”之事业。
五、
本书作为复旦通识教育读本系列中的一册,兼有研究和教学的双重使命。复旦的通识课程具有重视经典阅读的传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作为一本文史和社会科学经典的地位毋庸置疑。它以内容丰富、语言艰涩难读而著称。该书目前虽然有多个中译本,但仍然存在大量误读和误解;此外,这本书涉及多个学科的方法论,而且本国的国民教育中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由于跨越了多个学科——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也给读者造成了不少认知困难。近几年本人在通识课程授课过程中采用了“三位一体”的教学设计思路:即以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为基础;引入个人对诸如职业、财富、金钱等问题伦理思考,来拉近经典文本和当代学生之间的关联;其次,通过介绍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理性化,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在长时段的比较凸显文化意识,以此来提升人文素养。最后,要通过介绍和反思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和经济史等几个学科的方法论,来夯实学生的跨学科学术基础。
笔者认为“功夫在诗外”,无法顺畅理解该书的主要障碍并非原注的文本和文字,而是由于读者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知识预备。为了克服上述的困难,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力:第一,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建构韦伯新教伦理研究的文化史和作者的个人生活背景(第二-五章),以此来帮助读者了解韦伯进行新教伦理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以及他当时的主要问题意识。第二,要在经典文本和当代读者(尤其是当代中国大学生)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新教伦理中对财富、职业的一些论述,对于当代人的生活无疑可以提供一定的反思对照。因此本书在导论(第一章)中突出于了“伦理”在韦伯那里的特殊含义以及当代人所处的伦理危机,并在行文中引入了一些贴近生活的案例来阐释韦伯的一些核心概念,例如合理主义等。第三,有必要突出韦伯的方法论基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了韦伯的经济史案例研究和方法论反思。因此本书在第六章中概述了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不仅让读者看到韦伯说了什么,而且要让读者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第四,需要拓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中的论述,将视域拉回到亚洲和中国,加深读者的切身感。因此本书在第十二章中介绍了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中华文明的论述,以及二战后亚洲学者对其观念的质疑和反驳,以此来反思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比较文化的立场来反观中华文化的特质。第五,要同时避免神话韦伯和对韦伯的误读。因此本书在第十三至十六章中特别总结了对韦伯命题的批评和汉语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研究的典型误读,以及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新教教派研究之学术意义。第六,上述所有一切都必须基于对文本的直接和深度阅读。因此本书在第七到十一章重构韦伯论述的主要脉络和论证要点,正好对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五章内容。第七,在全书有四个附录。第一个附录给出了对基督宗教的概述,来帮助中文读者领会该研究的欧洲历史背景;第二个附录给出了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各章节的指导性问题,可以让读者在阅读前就带着问题进入文本。第三个附录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各章节内容和论证脉络的梳理,以防止在阅读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错失了韦伯的论证主线。第四个附录给意犹未尽的读者推荐了一些扩展阅读书目,当然其中的评价都是笔者个人的主观判断。
可以说本书期待的是一个频谱相对较宽的读者群,从对该文史社科感兴趣的普罗大众,到在校的大学生,再到专业的研究者不一而足。也请各位读者各取所需,不吝赐教。
每一代知识精英都认为自己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而每一个同时代的享乐者却没有这种危机感。他们认为所有的时代都是类似的——一样的平庸和一样的匮乏,或者同样的享乐和同样的混乱——不同的仅仅是一个人身处的社会阶层和地理位置。在知识精英看来,后一种立场恰恰是前一种危机的原因之一。横亘在两个群体之间的大概就是深度的学术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绝对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却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提问先于回答。诊断先于治疗。是为序。